“城市空间”中生命政治的双重维度——从“规训身体”到“调节人口”
时间:2020年04月09日 分类:文学论文 次数:
摘要:“空间权力化”是贯穿福柯政治权力批判的重要线索之一。作为“空间理论”的具体表现形式,对“城市空间”的分析集中体现出其对生命权力运行机制的剖析与反思。从这一视角考察福柯的权力机制,既是分析其生命政治学的重要切入点,也能够同时开启福柯现代性批判之城市空间向度的新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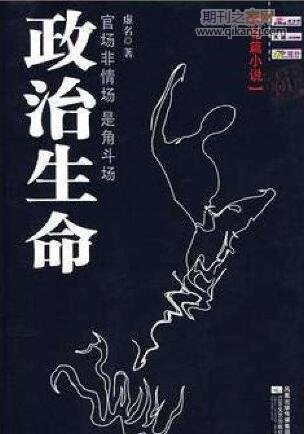
在福柯看来,17、18世纪历史的重要特征,就是“城市问题”取代“领土问题”成为首要问题,并且被整合进权力的中心机制。从“城市空间”问题可以看出,不论是城市建构中的空间区划与建筑设计,还是城市边界由封闭性到流通性的转变,都是政治权力运作结果,最终都指向生命政治学的双重维度:“规训身体”与“调节人口”。在司法机制、规训机制,尤其是安全机制的共同运作下,生命权力作用的目标由身体转变为人口。由此,公共管理作为新治理艺术之一诞生,成为城市空间中人口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城市空间;权力;规训;治理;人口
在《另类空间》中米歇尔·福柯指出,如果说19世纪人们痴迷于历史,影响世界发展进程的是历史不同主题的发展、中止、危机与循环,那么20世纪则是空间的纪元,代表着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通过对西方空间本身的历史的粗略回顾,福柯认为,我们的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与时间的关系更甚。人类生存所面临的空间危机与空间困境,使空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他自身正是以独到的眼光关照空间性的主要哲学家之一。福柯承认,正是长久以来对空间权力思想的探索和分析,使他实现了所追寻的根本目标,即阐发权力与知识间可能存在的各种关系。对福柯而言,抽象的权力话语转化成实际权力关系的关键,就在于各种各样的空间场域的支撑。换句话说,“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
①对于大部分的社会而言,空间与时间相比,更具有关键性,更具有精妙的表征意义。一部完全的历史有待撰写成空间的历史,而空间的历史同时也是权力的历史。各种权力机制的运作渗透到每一个空间中的每一个地方,既包括地缘政治学的重大策略与细微的居住策略,也包括城市中建筑的设计与空间的分配。因此,空间成为权力运作的重要场域。由此可见,不同于福柯的老师巴什拉在《空间诗学》中对直觉空间、梦想空间和激情空间等内部空间的分析,福柯的空间思想聚焦于外部空间,直接面向人的现实社会生活。
福柯指出,我们居住和生活的空间并不是一个仅仅用于安置自身与事物的虚空,而是一组组关系。这些关系关乎人们相互共存的形式:人们生活在一起、繁衍生息、每个人都需要一定数量的食物和空气来呼吸和维持生存,一起工作并从事不同或相似的职业。也就是说,人类生活空间的问题不仅是探寻空间容纳性的问题,“而且也是在一个既定情境中,了解人类元素的亲疏关系、储存、流动、制造与分类,以达成既定目标的问题”。①这里的“既定情境”的代表之一就是人们紧密共存于其中的“城市空间”,而“既定目标”是实现对城市中主体的治理。在17、18世纪,“城市被整合进权力的中心机制,或者更应该说,反过来,城市成为首要的问题,比领土问题更重要”。
②福柯发现从这一时期开始,所有将政治学当成人之统治艺术的讨论,都加入了一系列论述城市的空间规划、公共设施和住宅的兴建、卫生以及私人建筑的章节,用以维持社会秩序、避免传染病、保证道德的家庭生活等,而这些行为在本质上都凸显出生命政治学的双重维度———“规训身体”与“调节人口”。从城市的空间区划和空间形态的视角看待福柯的权力机制,既是分析其生命政治权力运作模式的主要切入点之一,也能开启福柯现代性批判之城市空间向度的新视野,为现代城市治理提供宝贵的理论资源和借鉴意义。
一、城市建构的本质:规训与治理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人与人之间社会联系的高级形式。城市空间是由各种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络系统,在这一空间中密集居住着具有异质性的人口。福柯指出,在17世纪及18世纪初,领土中的城市空间与其他地区相比有三个特点,一是城市中法律功能与行政功能的出现与完善;二是城市被限制在一个紧密的封闭围墙中,承担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功能;三是与农村相比,城市在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异质性程度高于其他区域。基于城市空间的特点,服务于社会统治、城市管理的技术和功能于18世纪起开始出现和发展,为关于这一空间的讨论增添了政治的向度与意义。
为了更好地在城市中进行政治权力运作,统治者首先需要对城市的空间进行建构。根据福柯的考察,西方的国家发展依次经历了三个阶段:中世纪时期的集权国家、近代社会的行政国家与现代社会的人口治理国家。与此相应,司法-法律机制、规训机制和安全机制成为三种主要治理形式。从这三种机制对城市空间的不同处理方式可以看出,不论所建构的城市在地理位置、几何图形方面有何种特点,都能够支撑其政治权力的完美运作;不论以何种组织方式分配空间、建构城市,其本质都是对身体的规训和对人口的治理。司法-法律机制对城市空间的建构主要体现在宏观层面。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福柯以亚历山大·勒麦特尔的文本《论首府》为例指出,城市的规划布局可以依照领土最一般、最综合的范畴来设想。如果把国家视为一个大厦,那么就要用整体的眼光来看待城市,以保证城市的各种需求。
《论首府》以两个问题为线索展开,通过对“国家是否必须有首都”和“首都由什么构成”的追问,勒麦特尔试图建构一个能够确保高度“首都化”的国家。在他看来,国家是由三个要素、三种秩序、三个阶层组成的大厦。大厦底层的坚实基础由农民构成,所有的农民(而且只能是农民)必须住在乡村。大厦的中间部分为由工匠构成的服务层,所有的工匠(而且只能是工匠)必须住在小城市。
而大厦的高层则是君主及君主的官僚,同样,君主和他的官僚,以及对宫廷的正常运作必不可少的工匠和商人,必须住在首都。从几何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好的国家不能是狭长的或不规则的,而必须具备圆的形式,且首都的位置应位于圆心。这虽然只是带有乌托邦性质的虚构方案,在现实中很难确保一个国家以作为政治、商业流通中心和主权所在地的首都为绝对中心而恰当的建构起来。但在福柯看来,勒麦特尔的可取之处在于他把主权的政治功效与空间的分配关联起来,这“实质上是以主权的概念对城市进行的界定和反思”。
①通过“主权”这一坐标,某些城市的特别功能,比如经济的、道德的、行政的功能就可以被依次建构起来。规训机制对城市空间的建构主要体现在微观层面。如果说在《论首府》中,人们依整个领土为模型对城市空间进行规划和建构,那么城市建构的另一种路径,是在一个比它自己更小的几何图形基础上进行的,那是一种具体呈现为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建筑学的模型,它们接下来会被分为更小的长方形或正方形。其中,军营就是一种著名的典型范例。
在完美的军营里,一切权力都将通过严格的监视来实施,任何一个指令都将成为权力运行的一部分。在这一权力活动中心内,权力极其强大、周密、有效。福柯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军营模式,至少是它的基本原则———层级监视的空间‘雀巢’———体现在城市发展中,体现在工人阶级居住区、医院、收容所、监狱和学校的建设中。这是一种‘嵌入’(encastrement)原则。”②以罗马军营为例,这是一种典型的规划精良的建筑,它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在新教国家复兴,在军事制度中作为基本的规训工具被重新应用。在罗马军营这一模型的基础上,不论是17世纪法国城市黎塞留(Richelieu)、克里斯蒂安尼亚,还是哥德堡的空间建构,都同样依照了军营的式样。与《论首府》的城市建构中圆与圆心的中心对称原则不同,以罗马军营为模型的建构是通过精心设计的不对称来规划和运作的。黎塞留中的城市空间是一个大长方形,其中一条中心街道将其划分为两个长方形。
其他的街道或与中心街道平行,或与其垂直,但由于彼此间距离不等、远近不同,城市被划分为一个个面积不同的长方形。其中,最小的长方形位于城市一端的边缘,格子最紧密且道路狭窄,是用于贸易的商业区域。最大的长方形位于城市的另一端的边缘,格子最宽且道路宽广,是普通居民的住宅区。在居住区中,商人和工匠家庭住在小的、外围街道上的住宅里,而主轴旁最巨大的奢华住宅,则分配给有名望的大人物。这意味着城市空间中严格的等级划分。由此可见,在对城市空间的建构中,贯穿着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的相互作用。而不论是微观还是宏观,不论城市空间是中心对称还是非对称的,其关键都在于将法律、规范施加并内化于主体。勒麦特尔建构的城市空间具有完美的中心对称性。
当首都与整个领土之间的位置关系符合圆与圆心的几何学图式时,既可以将法律植入领土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成员,避免任何地方、任何成员脱离法律和王权秩序,又可以履行首都的道德教化的职能,监视并支配人们的行为举止;既能够通过商品贸易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还可以把社会各阶层严格区分开来,确保统治者的地位并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黎塞留的城市空间虽然不具有中心对称性,但是就其对人的规训而言,却与勒麦特尔的城市有异曲同工之处。在黎塞留,空间的纪律秩序是塑造市集广场、住宅、教堂等城市配置的基础。在这个自我封闭的空间中,一个分层的、可见的和功能性的秩序得以建立与维持。这种城市空间的设计,“不只是作为阶级支配与剥削的装置而运作,同时也作为一个形塑过程,缠绕并监视居住其间的每一个人”。
③当这种城市空间结构延伸到大部分的西方城市中时,福柯生命政治学中“规训身体”的维度得以完美运作。随着18世纪西欧人口大增长的来临,“身体”———个人的身体和国民人口的身体状况呈现为一个紧迫性问题,成为监督、分析、干预、调整的目标和对象。于是,生命权力的另一维度:对人口的调节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一群活着的人组成的人口,这一特定现象,使得治理实践必须面对这些问题”①。“要使国家强盛,人口问题或许是最大、最活跃的要素。就此,健康、出生率、卫生,理所当然地在其中找到了重要的位置。”②为了解决一系列人口问题,包括城市人口统计、年龄结构计算、预期寿命和死亡率计算、城市人口健康状况控制等方案在内的人口技术被创设出来,并藉由安全机制展开。在建构城市空间时,安全机制精准界定并完美运用“环境”概念,结合环境治理的因素选定城市和规划空间,对人口施以持续不断的分析与操控。事实上,在“环境”观念确定成形之前,安全机制就已经在运作、装配、组织乃至布置一个环境。福柯从多角度对“环境”概念进行阐发,并且指出,不仅生命属于环境的组成部分,而且环境也是生命的组成部分。首先,“环境是一系列自然条件,河流、沼泽、山峦;以及一系列人为条件,个体的聚集,房屋的汇聚,等等”。
其次,“环境是一定数量的效果,这些群体的效果作用在所有在这个环境中生存的个体身上”。最后,福柯通过与“主权”和“规训”的对比,彰显出“环境”的深层内涵,“环境显示为一个干预的场域,这个干预不是针对能够自由行动的法律主体,这是涉及主权的情形;也不是针对多种多样的可以完成任务的组织和机体,这是规训要求的表现;而是试图精确地影响人口(population)。我指的是复杂多样的个人,这些个体根本上来说只以生物学的方式与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物质性发生关系。”③这里的人口既是统计学的对象,又是一个政治实体:全体人民。在此基础上,以安全机制为主导的城市空间建构,首先要开辟若干条穿越城市的线路和足够宽的街道,以确保四项功能:卫生与通风、城市内的交易、货物的集散和对海关的控制,以及对所有人的监视。此时,“环境”成为安全机制干预的主要目标,这种对于既包含人为因素又包含自然因素的环境的治理,同时也是对环境中人口的治理。于是,政治权力的作用点由具体的个人转向环境中的人口,转向对带有某种抽象性质的群体的调节。
二、城市空间的边界:由封闭到流通
在福柯看来,政治权力的运作不仅体现为城市空间的建构,也延伸至对城市空间的边界的管控,体现为由“封闭”到“流通”的转变。随着环境中经济、人口、司法、行政等因素的改变,城市中出现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状况。从经济发展来看,城市与其近郊之间的经济交换、商品贸易需求的增多,要求城市由封闭束缚走向开放流通;从人口数量来看,18世纪城市人口的大幅增长,使得城市封闭围墙内居住空间的拥挤成为问题;从人口健康来看,城市空间有它本身的危险性———疾病。
如中世纪肆虐横行的麻风病和鼠疫,1830—1880年间的霍乱等传染病,同样指向城市的区间隔离和空气流通的问题。福柯对此指出:“大体上说,18世纪的问题就是城市在空间上、司法上、行政上和经济上开放的问题:使城市重新进入一个循环流通的空间。”④流通包括人员的流通、货物的流通、空气的流通等诸多方面,对于18世纪的城市来说,循环流通是其发展的根本问题。城市边界由封闭到流通的过渡,一方面根源于主导机制由主权机制、规训机制向安全机制的转变,另一方面也根源于生命权力的维度由“规训身体”向“治理人口”的转变。
三、城市人口的治理:公共管理的诞生
由上文可以看出,在城市空间的政治权力运作中,管理生命的权力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规训身体”(以身体为目标、以惩戒技术为工具)与“调节人口”(以人口为目标、以安全配置为工具)构成生命权力机制展开的两极,并逐渐由前者转变为后者。如上文所述,两种形式之间不是正反题的关系,所谓的“转变”也不是前后相继、互相取代,而是主导因素的改变。
此外,这种转变不发生在政治理论的层面上,而是体现在权力的机制、技术、工艺的层面上,对“城市空间”中权力运作机制的“毛细血管式”解剖,是福柯进行现代性批判的独特视角。如果说马克思以资本逻辑的宏观视角反思现代性,大卫·哈维、列斐伏尔以资本运作的空间视角批判现代性,那么福柯则着眼于权力机制,将其与空间批判结合起来,从生命权力(生命政治)的微观视角切入现代性问题。具体来看,福柯对城市治理、城市空间的考察主要着眼于现代城市,这一考察构成其现代性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提出的“规训身体”与“调节人口”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问题。随着微观权力的重心从前者到后者的倾斜,针对城市人口调节的“公共管理”作为新治理艺术之一开始发挥作用。正是在此,福柯洞察到现代性治理的奥秘。为了清楚地分析三种权力技术(司法-法律技术、规训技术、安全技术)的内在联系,揭示城市空间中“公共管理”艺术对人口的治理,我们首先需要追溯权力机制的发展过程。
四、结语
综上,城市是支撑着权力在其中充分运作的空间。在面对城市空间问题时,“主权将领土首都中心化,提出了政府位置的主要问题,规训架构起一个空间并且提出要素的等级和功能分配的关键问题”,安全则试图治理环境(milieu)。②在司法机制、规训机制,尤其是安全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城市空间的每一个角落都展现出生命政治的双重维度———“规训身体”与“调节人口”。
从司法-法律机制对城市空间的宏观建构,到规训机制对城市空间配置与区划,再到安全机制对环境概念的巧妙应用;从城市边界的封闭性到城市中人员、货物、空气等元素的流通性问题;从人口概念的出现到公共管理对城市、国家的管控,最终都指向对身体的规训或人口的治理,并逐渐由前者过渡到后者。在城市空间中,一系列“调节人口”的措施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关注人口的身体健康、保证人口的理想寿命,还规划人口的职业、评估居民之间的财富关系。既有可能为个体的自由和个性发展创造空间,又将微观政治权力扩张到对生命的管理,渗透到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从本质上看,城市空间中的人口治理问题本质上是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具体构成部分。
“现代性”看似是一个具有“无定性”的宽泛概念,思想家们至今尚未在内容和范围等方面达成共识。但毋庸置疑的是,就其精神内核而言,不同的现代性概念所表征的都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生命活动和生存世界的真实观照。不论是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理性批判,还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资本逻辑剖析;不论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技术理性批判,还是以奈格里、哈特等激进左翼思想家为代表的“另类现代性”反思,虽然其思想路径、逻辑视角不尽相同,但都蕴含着与其时代相符的独特的生命内涵和价值精神。因此,“现代性”概念的“不定性”所体现的正是其自由性、开放性和创造性。就此而言,福柯所揭示的“城市空间”中生命政治的双重维度———“规训身体”与“调节人口”,是他以独有的方式对人类生存状况中最深邃精微、最不易察觉之处所进行的深刻表征。
如果说马克思从资本逻辑的宏观视角对现代性进行前提批判,那么福柯则以政治权力的微观视角为切入点。他的理论将微观权力与城市空间相结合,侧重于对渗透在个体身体与整体人口的“毛细血管式”的权力进行细微分析,既开拓了微观政治权力研究的新视野,为现代城市治理提供了宝贵理论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的深化与补充。然而,尽管福柯也曾经揭示“身体规训”“调节人口”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却并未在宏观层面进行系统的诊断。他的城市治理思想必须以马克思的理论为背景和支撑,才能更加完整和具体,从而“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①
马克思主义论文投稿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月刊)是全国唯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体系为宗旨的大型学术理论刊物。本刊面向现实、面向当代,刊登探讨深层次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论文,提供丰富的国内外研究动态和信息,是一切从事教学、科研和宣传的理论工作者、大专院校师生、党政干部以及所有关心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人们的忠实朋友。
SCI论文
- 2024-10-23SCI期刊要自己推荐审稿人 推荐谁
- 2023-08-01sci四区发论文最容易吗
- 2023-05-10英文论文的检索号是什么
SSCI论文
- 2023-03-08全球经济趋势分析论文发表ssci期
- 2024-02-02学霸笔记:超级好用的ssci论文发
- 2024-03-22SSCI四区的文学期刊
EI论文
- 2022-08-12发表scopus论文的步骤
- 2023-05-31纺织类的ei期刊(3-5本)
- 2022-11-11ei会议论文会拒稿吗
SCOPUS
- 2023-04-21论文被scopus成功录用需要多长时
- 2023-03-14scopus期刊收研究生论文吗
- 2023-02-20scopus检索与ei哪个好
翻译润色
- 2023-05-06基因测序文章怎么翻译润色
- 2024-08-17国际中文期刊评职称承认吗
- 2022-05-07sci论文润色更容易录用吗
期刊知识
- 2020-02-07sci期刊发表的论文都可以被web o
- 2022-03-08火电厂论文外文翻译有什么服务
- 2021-01-16高钾血症论文发表期刊
发表指导
- 2021-08-07电熔炉相关论文文献看哪些
- 2018-04-04经济学动态发表论文审稿周期多久
- 2024-08-17氧菌论文可以投稿的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