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文学期刊发表托洛茨基的评价
时间:2015年12月27日 分类:推荐论文 次数:
本篇文章是由《文学与文化》发表的一篇文学论文,本刊秉承开发而严谨的学术品格,以深入研究古今中外文学为核心主旨,同时注重突出文学与文化的关联性。创刊后,刊物得到了诸多学界同仁的鼎力支持,海内外众多文学文化研究者不断赐稿,多篇文章为《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所节录或转载,获得了良好的学术影响。
偶然在《视界》上读到杜建国先生的大文〈托洛茨基的真实面貌〉(《视界》第6辑,2002年4月,以下简称〈托文〉)。真没想到现在也还有人对托洛茨基有兴趣,而且作的又是翻案文章,自然多了几分注意。但读过之后,却发现问题多多,尤其是在关涉托氏评价、以及对一些相关的史实和理论问题的读解上,作者的看法或过于简单、片面,或似是而非,让人不吐不快,且写出来,与作者一同讨论。
问题一:关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异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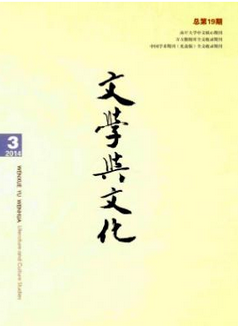
从切入点看,作者写此文似是为反驳郑异凡先生的〈由「先知」引起的话题〉一文(载《读书》1999年第五期),这本属正常。但我不知作者哪来的那么大的情绪,以至文中对郑异凡先生的多处指责都有欠厚道,有些指责甚至连逻辑都不顾。比如,作者在谈到郑先生对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比较分析时,引了郑先生一句认为托氏与斯氏是「不共戴天的死对头」的话,然后又引了郑先生「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是托洛茨基予以肯定的」,「斯大林的实践是托洛茨基所鼓吹的工业化的一面镜子」,「斯大林以消灭富农为起点在农村实行集体(化)」是「符合托洛茨基的主张的」等语,理直气壮地反问道:「既然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主张大同小异,那么他们又怎么会不共戴天的呢?」1这就很让人惊讶,「主张大同小异」就不可能「不共戴天」了吗?除了主张,还有性格、气质、以及个人恩怨、权力之争等等,都是足以造成「不共戴天」的因素。特别是具体到托洛茨基与斯大林而言,命运注定这两个人几乎是从一见面开始就处于互相敌视的位置,以至列宁逝前还在担心他们两人发生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党的分裂2。这种同中有异──不是因为政见,而是因为其它原因形成的对立和冲突的情况,尤其在政治人物中并不鲜见。而况「主张大同小异」一语并非郑先生原话(对于托氏与斯氏的「主张」而言,是不好以简单的「异同」论之。上文因只考虑逻辑,对此未作甄别,下文将详论之),但作者只顾倾倒心中的愤懑,似乎顾不了这许多,仍沿着自己的逻辑挺进,紧接着竟发出了这样令人吃惊的责难:「尤其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郑异凡先生竟是在读了《先知三部曲》后来重复这种评价的,因为正是《先知三部曲》推翻了这种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如果不是说诬蔑的话。」3
且不说《先知三部曲》是否「推翻了这种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尚需查证(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凭常理也该明白:别说《三部曲》的作者多伊彻本人就是个托洛茨基主义的热烈拥护者、崇尚者,他的著述和评价也只能算一家之言,就算他不偏不倚,真正做到了客观公正、全面准确,也不可能定于一尊,谁都不能表示不同意见;谁读了《三部曲》,谁就只有双手赞成的权利!?这叫甚么学术?恐怕多伊彻本人也不会如此缺乏自知之明吧?
更重要的是,所谓「这种对托洛茨基的评价 」──即托氏早先提出来的加速工业化与集体化的主张 ,后来由斯大林所实现的说法,并不是郑异凡先生一个人的看法,而是国际学术界中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如果不能说公认的话。因此,包括《先知三部曲》在内,基本上持的也是这一观点,不知作者为何视而不见。且引几段如下4: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左倾方针持一种相对赞赏的看法,承认它的积极意义。这一事实使托洛茨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甚至把他们搞胡涂了。
在十月革命11周年庆祝日,从莫斯科红场上传出的官方口号是:「警惕右倾危险!」「打击富农!」「抑制耐普曼!」「加速工业化!」这些口号响彻了整个国家,扩散到了最边远的角落,甚至也传到了阿拉木图。这正是托洛茨基长期以来试图说服党采取的政策!……可以这样认为,执政派现在被迫抄袭托洛茨基的思想,这一事实就是为反对派所作的最好辩解。
这两个对手的命运就是这样古怪,当托洛茨基被驱逐出俄国之时,斯大林却着手以野蛮的方式消灭俄国的落后和野蛮,仿佛是要经典马克思主义回流,而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将要实现托洛茨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纲领。托洛茨基是二次革命的真正鼓吹者和宣导人,但在其后的十年中,斯大林却是它的执行者。
引文未免累赘,却又必不可少。只不过,他们两人的关系事实上远比这里说的要复杂得多。
从性格上讲,在俄共的早期政治领袖中,恐怕再难找出有哪两位像斯、托二人这样,有着那么多的相似与差别了。同样的倨傲、自负,同样的不甘人下,有着强烈的领袖欲,并且同样的倾慕权力,同样的敏感自尊,喜好虚荣。犹如同性相斥的磁场原理,过多的相似也产生了太大的差别:他们一个热情似火,一个却冷静如铁。一个雄辩滔滔,长于辞令;一个却沉默寡言但更精于算计。一个喜欢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尤其乐于置身在漩涡中心,与革命进行亲密接触,直接对话;另一个却更喜欢侧身一边默默做着党所交给他的工作。与语言乏味,举止粗俗的斯大林相比,才气纵横的托洛茨基往往显得更有教养,也更注意风度。托氏是思想家、革命家,比斯氏更擅长理论的创建,真率之外,更不乏几分革命骑士的浪漫和理论家的坦诚,他相信理论的力量远远超过他相信政权的力量,因而也常有为理论所累的时候。斯大林则是个务实的行政主义者,与理论相比,他显然更迷信组织,更相信权力。身为党的总书记,他也是把行政能量发挥到极致的权术大师。他的政治哲学实则有着太多的马基雅维里成分,骨子里又带了几分拜占庭阴谋家的气质,常常在不动声色之中就能置对手于死地。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铁腕人物,对大权在握,发号施令有着同样的喜好。别看托洛茨基老在民主问题上向斯大林主流派发难,但只要想一想他在内战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对行政命令主义的过分依赖(或许正是列宁所批评的「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以及他天性中喜欢纪律与服从的强制性格倾向,再想一想他对工人反对派的厉声呵斥,以及在工会问题争论中对军事共产主义强制方法的偏爱(「拧紧螺丝钉」、「整刷工会」等)等等,不难想象一旦大权在握后的托氏会是甚么样5──尽管不会与斯大林完全一样!
不过,即使如此,从政治主张上讲,斯、托两人确实是不好将其放到一起,简单地论其异同的,原因很简单,就「主张」而论,托氏有理论,而斯氏没有理论。具体到工业化和集体化问题而言,斯大林最初反对托洛茨基等人要求加快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进程,并非是真的认为这会中断新经济政策,影响工农两大阶级的结盟,而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拱卫自己列宁继承人的正统形象,稳固自己的权力。所以,出面与托氏等人进行理论争辩的主要是布哈林,而不是斯大林。而斯氏在后来转向,以托氏也无法赞同的激烈手段和速度,迅猛推行集体化与工业化的方针,也并非是害怕农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害怕社会主义受到削弱,而是从粮食收购危机中看到了农民反抗的可怕,因此亟欲要将之纳入庞大而又严密的官僚化计划体制(当然也是行政组织体制)的控制之下。所以,他要抛弃布哈林,转而向托洛茨基派的理论求救,并故作慷慨地接受了许多反对派骨干的「投诚」,以至连托洛茨基本人也一度判断失误,想在斯大林需要他们的时候伸手相援,与斯氏结盟来反对布哈林。实际上,斯大林心里压根就不会原谅反对派──他们的最终结局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即使他最终执行了托氏的纲领,也不好就说他的主张与托氏「大同小异」。对斯大林来说,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以至后来居然敢与德国法西斯结盟瓜分波兰,那么,要不要搞工业化和集体化,就只是个为我所用的问题,而不存在甚么剽窃与认同的嫌疑。一句话,这只是斯大林为实现他的独裁之路所要跨越的一道小小的障碍而已。
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郑异凡先生并没有简单地说他们的主张「大同小异」,而只是说「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是托洛茨基予以肯定的」,说「斯大林的实践是托洛茨基所鼓吹的工业化的一面镜子」等等,应该说,话还是讲得颇有分寸的,由此得出「只有托洛茨基『同布哈林的争论才是两种社会主义建设方法的争论』」也并没有甚么错,与「不共载天」的说法也并不自相矛盾。至于讲到托氏的主张至少在时间上与方法上跟斯氏的集体化工业化不同──正像〈托文〉作者在文中所一再争辩的那样,那么,我想提醒作者注意:这其中除了托氏提出的仅仅只是理论而斯氏实行的又仅仅只是结果的差别之外,也还有一个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问题。对于理论逻辑,多伊彻就曾提到这样一个细节:当托洛茨基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大家完成伟大而艰巨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任务时,克拉辛曾向他问道,他是否充分考虑过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含义?并向他提到早期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通过残酷的殖民掠夺,摧毁英格兰的自耕农,摧毁印度的家庭纺织业等等,才得以完成的。「正是在『印度平原白茫茫』一片尸骨之上,现代纺织业才得以兴起。」据说,托洛茨基听后,当时就跳起来抗议说,他的建议「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对此,多伊彻写道:「这当然不错。但不管怎样,他的立场的逻辑发展不就是将导致『对农民的掠夺』吗?」6据多伊彻说,此后,托洛茨基便很少再使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一语了。也许他已觉察到包含在这一「规律」中的那层不详的阴影?
至于历史逻辑,多伊彻曾针对按照托洛茨基的路子历史会怎样的设问,讲过这样一番颇为深刻、透彻的话7:
如果要问:托洛茨基会把这次革命引向何方?他是否既能使广大苏联人民免遭斯大林统治下所受的损失、贫困和压迫,同时也能以相同的速度和规模实现工业化?或者他能说服而不是强迫农民合作经营农业?进行这样的推测毫无意义,这些问题是不可回答的……事实上,20年代的政治演变已事先决定了30年代俄国社会改造得以完成的道路。这一演变导致独裁和铁的纪律,进而导致了强行的工业化和集体化。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所需的政治工具在20年代就早已造好了。
问题二:关于新经济政策
1926年,在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成联合反对派同斯大林主流派的争论中,新经济政策是个焦点。尽管由于新经济政策是列宁生前所订,在令人崇敬的领袖刚刚去世之后,谁也不会去冒触犯列宁思想遗产的风险,因而,表面上并没有人对新经济政策直接提出批评。但从托氏等人关于加速工业化,加强计划化和集体化,以及出于对农村资本主义因素增长的忧虑而提出的限制富农,对富农课以重税等主张中,还是不难看出,根子就在新经济政策!这是关键,也是双方分歧的实质之一。
无论是从当时还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新经济政策的真正意义,是在于它启动了被革命和战争打断了的市场机制,开启了一条通向市场经济的大门。恰恰是这一点,与人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明显不符,因此,新经济政策实行之初就在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列宁为此而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并将之解释为一种暂时的「退却」,一种「迂回曲折」的进攻。在随后的几年里,列宁为新经济政策倾注了大量心血,写了不少文章,不断发现和挖掘新经济政策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给予新的阐释和提升。大体说来,列宁赋予了新经济政策这样几重意义:
(1)是从非常态的战时体制转向常态的和平建设体制的一种过渡8。在强制与半强制的战时体制下,你可以用超经济方法向农民强行征集「余粮」──或者像列宁后来所说的那样,有时甚至是农民的「必需粮」,但在和平体制下,你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余粮收集制后来引发的严重危机、动荡和全国雪片一般的抗议都已证明:农民决不允许将强制的战时纪律永远盘旋在他们头上!
(2)新经济政策是工农两大阶级政治联盟的经济基石。平等的联盟,必须以平等的交换关系作基础,否则,政治平等就无法得到保障。「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它在哪里?在同农民进行商品交换!!」9
(3)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适应于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建设道路、建设方法,它「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10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占多数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不能抛弃小农,而必须采取与之结盟的战略,为此,就需要找到一种适合他们,为他们所乐于接受的方法,以便在自愿和平等的基础上,改造他们,带领他们一同走上社会主义。改造小农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所以,新经济政策也是长期的。
然而,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很多布尔什维克高层领导却一直未能认识到,新经济政策实则是从战时体制转向和平常规体制的一次根本性的战略转移!他们恪守着某些战时共产主义的也是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信条和思想原则,将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把商品关系、市场原则等同于资本主义,视个体劳动为危险的自发资本主义势力,所以,对新经济政策实行几年后重新活跃起来的农村经济状况和市场经济关系作出了片面的、也是夸张的估价。
不错,托洛茨基本人早在20年初就曾提出过实行粮食税的建议。多年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11:
我从乌拉尔带回大量有关经济情况的考察报告,这些报告的结论,一言以蔽之:必须抛弃战时共产主义。我的实地调查使我相信,因内战条件强加于我们的战时共产主义方式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恢复我们的经济生活,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引进个人利益的成分;换言之,必须恢复某种程度的国内市场。我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一个方案,计划用一种征收粮食税的办法来取代征粮制,并恢复商品交换。
但事实上,托洛茨基当时的认识远不像他后来所标榜的那样,似乎已真的看透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本质,否则,他就不会在自己的建议被否决之后,立即又迅速祭起战时共产主义的法宝,并将之严厉地贯穿到铁路系统的整顿中,进而更提出了「劳动军事家化」,「拧紧螺丝钉」等加强战时体制的口号,由此挑起了一场关于「工会国家化」问题的争论。细观托氏在争论中的主张,他与列宁的分歧,实质上是一个要不要将战时原则继续运用于和平时期的问题。从托洛茨基后来的一系列主张及其表现看,应该说,托氏的思想一直都未能走出战时共产主义的迷雾。
SCI论文
- 2023-08-01sci四区发论文最容易吗
- 2023-05-10英文论文的检索号是什么
- 2024-10-23SCI期刊要自己推荐审稿人 推荐谁
SSCI论文
- 2024-03-22SSCI四区的文学期刊
- 2024-02-02学霸笔记:超级好用的ssci论文发
- 2023-03-08全球经济趋势分析论文发表ssci期
EI论文
- 2023-05-31纺织类的ei期刊(3-5本)
- 2022-08-12发表scopus论文的步骤
- 2022-11-11ei会议论文会拒稿吗
SCOPUS
- 2023-02-20scopus检索与ei哪个好
- 2023-04-21论文被scopus成功录用需要多长时
- 2023-03-14scopus期刊收研究生论文吗
翻译润色
- 2023-05-06基因测序文章怎么翻译润色
- 2022-05-07sci论文润色更容易录用吗
- 2024-08-17国际中文期刊评职称承认吗
期刊知识
- 2021-01-16高钾血症论文发表期刊
- 2022-03-08火电厂论文外文翻译有什么服务
- 2020-02-07sci期刊发表的论文都可以被web o
发表指导
- 2024-08-17氧菌论文可以投稿的期刊
- 2018-04-04经济学动态发表论文审稿周期多久
- 2021-08-07电熔炉相关论文文献看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