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论文沟通行动具备獨立性与优先性吗?
时间:2016年05月21日 分类:推荐论文 次数:
这篇逻辑学论文发表了沟通行动是否具备獨立性与优先性,探讨了哈贝马斯言语行为理论,在语用学的层面上,以言行事与以言取效即便能够在“形式”上进行区分,但在“经验”层次上却始终无法达到应有的稳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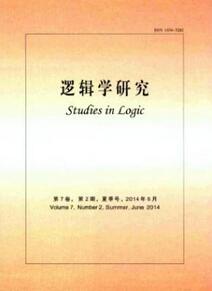
摘要: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旨在区分沟通理性和工具理性,而这一区分的关键在于能否有效地区分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特别是能否证明以言行事行为独立于并且优先于以言取效行为。本文认为哈贝马斯对这个根本问题的论证并不特别令人信服,在此意义上,哈贝马斯所构筑的沟通行动理论就存在根基不牢的危险。
关键词:逻辑学论文,沟通行动,策略行动
韦伯之后,任何对“现代性”做严肃思考的学者,无论赞成或者反对,几乎都无法绕过韦伯提出的问题,即现代性与理性化(rationalization)之间所存在的内在关联性。[1]哈贝马斯同样如此。不过在哈贝马斯看来,韦伯对现代性的诊断虽然不乏洞见,究其根本却是一个“误诊”,因为韦伯所预言的“铁笼”并非是密不透风、无路可走的绝地,身处其间的现代人依然有出逃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正蕴藏在对“启蒙的前提”,也即理性化概念的重塑之中。哈贝马斯重塑理性化概念的主要动作是,比照工具理性,提出沟通理性的概念与之分庭抗礼。事实上,整部《沟通行动理论》的任务就是“在日常实践和沟通实践自身中,在沟通理性被压制、被扭曲和被摧残之处,发现这种理性的顽强声音”。[2]而工具理性与沟通理性之间的区分,在哈贝马斯看来,又可以转化为策略行动与沟通行动的区分问题。本文认为,如果哈贝马斯能够成功地证明作为言语行动类型之一种的沟通行动(相对于策略行动的)的独立性乃至优先性,则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就已成功大半。因此如果借用康德式的提问方式,本文将主要检讨以下两个主要问题:1,作为言语行动类型之一种的沟通行动是否可能?2,如果可能,如何可能,以及如果不能,为何不能?
本文的基本结构如下:第一节,简述哈贝马斯对策略行动和沟通行动的区分,以及相应的对以言取效行为和以言行事行为的区分。第二节,简述沟通行动的有效性条件以及哈贝马斯对塞尔言语行为理论的批评。第三节,分别从四个方面批评哈贝马斯的言语行为理论,首先指出在语用学的层面上,以言行事行为与以言取效行为即便能够在“形式”上进行区分,但在“经验”层次上前者却始终无法达到应有的稳定性。其次,沟通行动之于策略行动的源初性即便是在哈贝马斯那里也是语多含糊。第三,哈贝马斯区分三个世界缺乏令人信服的理据。第四,哈贝马斯关于命令的言语行为分类同样存在不妥之处。
一,作为言语行动类型之一种的沟通行动是否可能?
在哈贝马斯看来,虽然沟通理性一直处于“被压制、被扭曲和被摧毁”的境遇,但是沟通理性之存在却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因此问沟通理性或者说沟通行动是否可能,就如同我们问知识是否可能一样荒谬。不过本文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沟通理性或者沟通行动是否可能,而在于“作为言语行动类型之一种”的沟通行动是否可能,说得更清楚一些,我们追问的是在言语行动分类中沟通行动能否取得与策略行动对等乃至优先的地位?惟其如此,我们才可以将沟通行动作为言语行动类型中的一个独立的、具有自主性的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沟通理性,以对抗工具理性的挑战。
要区分以成功为导向的策略行为和以达致理解为导向的沟通行为,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方面,沟通行为常常被用作策略行为的手段,两者经常发生混淆;另一方面,并非所有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行为都是以达致理解为导向的行为的案例,也就是说存在着无数非直接理解的言语行为。要克服上述两个困难,哈贝马斯认为必须证明以下这个观点:“在语言使用中,达到理解是源初的模式,而在此基础上的非直接理解以及对语言的工具化使用则是寄生的产物。”[3]而这个观点的澄清,则有待于援引奥斯丁的理论,也即对以言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s)和以言取效行为(perlocutinary acts)的区分。
奥斯丁三分言语行为类型,除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外,还有以言表意行为(locutionary acts)。[4] 以言表意行为是陈述某个事态,比如下雨了;以言行事行为是通过陈述某事做事(其公式是In saying X,I was doing Y),比如我向你道歉;以言取效行为则是指,说话者在说了些什么后通常还能对听者、说者或者其它人产生相应的确定后果(certain consequential effects),以言取效行为的公式是“By saying X,I did Y”。奥斯丁虽然区分了三种基本的言语行为,但实际上他并不很关心这三种行为的严格界定,也不完全拘泥于三种行为的字面意思,而认为“In saying X,I was doing Y”和“By saying X,I did Y”这两个公式并不可靠。[5]
奥斯丁的理论引起后人许多争论,问题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以言表意行为和以言行事行为的区分,一是以言行事行为与以言取效行为的区分。哈贝马斯显然更看重后一个区分,因为在他看来,沟通行动对应以言行事行为,策略行动对应以言取效行为,所以要论证沟通行动的源初性,就得首先论证以言行事相对以言取效的源初性。
奥斯丁本人对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做出了三个区分:首先,以言行事行为是约定俗成的,而以言取效行为则不是约定俗成的;其次,以言行事行为可以通过显式的以言行事公式得以澄清,而对以言取效行为不能使用这个公式;再次,以言行事行为实质上仅仅是说话带来什么效果的问题,是实际上发生了什么的问题,而以言取效行为不是说话的效果问题。[6]
哈贝马斯在奥斯丁的基础上,将以言行事行为与以言取效行为之间区分扩展为四种标准:
1,在一个以言行事行为里,说话者只要求听者理解这个言语行为明白晓畅的内容,他没有任何超出内容意义以外的企图;而一个以言取效的行为则不然,说话者希望听者明白的不只是言语行为的内容,而是说话者本人的意图(intention),就此而言以言取效行为等同于目的行动(teleological action)。[7]
2,一个以言行事行为要获得成功,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个言语表达中推论出其条件;而一个以言取效的行为是否成功,则无法从这个言语表达中推论得出。[8]比如,我向你承诺从香港带化妆品给你。就其为一个以言行事的例子言,只要你明白了这个表达的内容,它就成功了;但是就其为一个以言取效的例子言,或许我说这句话是为了博你欢心,然而结果却是你惶惶不安。
3,根据第二点,我们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以言行事的结果是和言语行动存在着约定俗成(conventionally regulated)的关系或者说内在(internal)的关系,而以言取效行为的后果和所表达的意义的关系却是外在的,一个言语行为的可能的以言取效后果取决于偶然的脉络,而不是如以言行事那样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9]
4,彼得•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用别的区分标准来替代约定俗成这个标准。一个说话者,如果想使他的行动成功,就不应该暴露他的以言取效的目的,相反,要想达成以言行事的目的却只能把它表达出来。以言行事是被公开地表达出来的;以言取效则不太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承认”。[10]
比较奥斯丁和哈贝马斯的观点,我们发现二者都认为以言行事与以言取效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以言行事的言语行动与其结果存在“约定俗成”的关系,而以言取效则不然。事实上,也正是这一点引发的争议最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三节再予以澄清。
通过区分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哈贝马斯进一步区分策略行为和沟通行为,他说:“我把这些言语行为称为沟通行为,在其中所有的参与者追求的是以言行事的目的,而且只追求以言行事的目的;另一方面,我把这些言语行为视作策略行为,在其中至少有一方的参与者试图通过他的言语行为对对方造成以言取效的后果”。[11]策略行为和沟通行为之间的区别对于形式语用学的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它表明一个言语行为既能用于相互理解也能用于策略性的目的。哈贝马斯批评奥斯丁没有发现这个重要的区别。哈贝马斯称:“奥斯丁没有把这两个例子区分为不同类型的互动,因为他倾向于把沟通行为,也就是达致理解的行为,等同于用言语行为协调的行动。他没有看到沟通行为或者言语行为可以用作其它行为的协调工具。‘沟通的行为’(也就是用言语行为协调的行动)不能和我所介绍的‘沟通行为’相混淆。”[12]
二,沟通行动的有效性条件以及哈贝马斯对塞尔的批评
目前为止,哈贝马斯虽然已经区分了沟通行动和策略行动,并且给出了沟通行动的基本定义,但是沟通行动的类型和结构仍然处在晦暗之中。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曾列举一系列“语言游戏”的例子,指出语言有各种不同的使用,但维特根斯坦没有对之做出详细的区分,相反他认为言语行为的类型有无数种。对此塞尔颇为不满,他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观点颇值得怀疑,因为既然“没有人会说有无数种经济制度、婚姻制度或政治党派;为什么语言就会比任何其它方面的人类社会生活更难加以分类呢?”[13]塞尔不仅认为事实上不存在像维特根斯坦和其它许多人宣称的那样有无数的或不定数的语言游戏或语言使用,而且指出“在任何语言哲学中最明显的问题之一是:有多少使用语言的方式?”[14]
塞尔用十二种维度来划分言语行为,其中最重要的三个维度是:1,以言行事的观点,以言行事决定了言语行为的主要语用功能;2,适应的方向(direction of fit),意思是言语行为的命题内容是如何与世界相关联的;3,说话者表达时的心理状态。根据上述三个原则,塞尔把以言行事行为区分为以下五种:断言的,指引的,承诺的,表情的,宣告的。
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塞尔的问题在于只使用一个世界的模式,由此导致的后果是许多分类彼此之间界限模糊。为此,哈贝马斯在三个世界的划分基础上,在有效性的宣称以及布勒的语用学功能的帮助下,把言语行为区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1,记事的。对应于客观世界的事态,是关于真理的宣称,其功能是用来表达事态的。例如,老师说“我向你保证窗子是开着的。”如果听者选择要批评这个言语行为,就意味着对由说话者给出的关于真理宣称的批评。听者也许会接受这个关于真理的宣称,如果他认识到说话者有很好的理由宣称他的命题为真。
2,表情的。对应于主观世界,是关于真诚性的宣称,用来表达说话者主观世界中的东西,例如,老师说:“我希望窗子是开着的。”如果听者选择批评这个言语行为,就意味着对说话者的真诚性的批评。说话者可以接受这个关于真诚性的宣称,如果说话者能够向听者确保他的确是在意指他所说的东西。如果听者仍然怀疑说话者的真诚性,那么说话者就只能在他随后的一致性行为中来展示他的真诚性。
3,规范的。与社会世界相关,是关于正当性的宣称。这类言语行为是用来规整社会世界中的行动者的互动的,比如老师说,“我请你打开窗子。”如果听者选择批评这个言语行为,他就是在挑战这个言语行为的规范正当性。听者也许会接受这个宣称,如果听者认识到使这个言语行为有效的规范脉络。
4,命令式。与客观世界相关,是关于权力的宣称。这类言语行为是说话者以听者必须如此这般的方式指称他所欲求的状态。比如,老师命令学生说:“开窗”。使听者接受这个言语行为的原因在于,说话者可以强迫听者去做,比如借助于惩罚。
哈贝马斯特别指出,前三种类型的言语行为属于沟通行为,而后一种类型即命令式则是策略行为。
在一个成功的沟通行动中,听者必须首先理解言语行为,然后必须还把这个言语行为作为有效的行为接受下来。这意味着听者可以根据有效性宣称中的命题内容为真性、真诚性和正当性来批评和控制这个言语行为。还举前面的例子:老师要求学生开窗,这时候老师有两种选择,或者采取沟通行动的方式,或者采取策略行动的方式。策略性的行为意味着,老师可以通过钱或者强力来迫使学生开窗;而沟通行为则意味着,老师首先是以言语行为来协调行动,并且学生可以对老师让学生开窗这个命令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如果学生理解这个请求、认为它是有效的而且也开了窗,那么这个社会互动就是一种成功的沟通行动;相反,如果老师让学生开窗但双方没有达成相互的理解,则就是一个策略行为的例子,比如老师可以威胁学生去开窗,而这时候强力就是使社会互动协调一致的手段。
三,小结
简述完哈贝马斯的言语行动理论,最后我想从四个方面检讨哈贝马斯的理论:第一,以言行事与以言取效行为的划分是否成立;第二,沟通行动和策略行动谁更具有优先性;第三,哈贝马斯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问题;以及最后,哈贝马斯关于命令的言语行为分类所存在的问题。
我们先来分析第一个问题,如前所述,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是否成功,首先取决于他对沟通行动和策略行动的区分是否成功,而这个问题又可以转化为以言行事行为与以言取效行为的区分是否成功。因此,我们首先要考量的就是哈贝马斯关于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之区分的证立是否成功。
如前所述,哈贝马斯与奥斯丁都认为,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的主要区别在于以言行事行为与其后果之间存在着“约定俗成”的关系,而以言取效行为与其后果之间则不存在这样的关系,所以问题的关键集中在究竟什么是“约定俗成”的关系?如果哈贝马斯能够证成上述观点,那么哈贝马斯就可以反推出沟通行动的确与策略行动存在界限分明的区别,并由此最终证成沟通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区分。
那么究竟什么是“约定俗成”的关系呢?
如果一个言语行为的效力保障来自于外在的社会规范或者强力,那么这个言语行为和以言行事的结果之间的确存在“约定俗成”的关系,比如在加油站里说“不准抽烟”,在公共场合说“不准吐痰”,此类言语行为的结果(一般而言)是抽烟者把烟掐了,吐痰者不再吐痰——但是这种约定俗成的关系不仅了无新意,而且由于它所依傍的是外在的规范和强力,而非理性论辩,所以也无助于沟通行动理论的澄清。
哈贝马斯当然不会这么没有创意。相反,他认为,问题恰恰产生在以下这种情况,即如果言语行为的权威既不是直接借自规范的社会力量(比如在加油站里说“不准抽烟”,在公共场合说“不准吐痰”这些与制度化相连的语言行为。),也不属于偶然促使同意的潜能(比如表达意志的命令句中),那么言语行为是从哪里得到力量来调节互动行动的?[15]
哈贝马斯认为,在一个达成理解的沟通行动里,听者接受这个言语行为的过程可分为三个层面:1,听者了解了这个陈述,也就是说,他把握了陈述的字面意义;2,通过回答“是”或者“不是”,听者给出自己的立场;3,在达到一个已经获得的同意的结果里,听者根据约定俗成的义务(conventionally fixed obligation)指导他的行动。[16]
为什么一个听者在没有外在规范的强制下,依然能够按约定俗成的方式行动,这种约定俗成的力量来自何方?这是一个问题。
以“窗子开着呢”这句话为例。
如果没头没脑地说一句“窗子开着呢”(就像早期语言哲学家讨论语义真理时所做的那样),它就是一个以言表意行为(locutionary action),或者说是一个记事性(constative)言语行为,表述的是“窗子开着”这么一个事态。
可是,在日常对话中,我们很少这么没头没脑的说话,否则我们就会被指责为“不可理喻”。设想一个场景,屋里都是人,我走进门突然说一句“窗子开着呢”,屋里的人肯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说:“一般而言,对于记事性言语行为的意义后面并不跟随特殊的义务(obligation)”[17]但是如果要想使这句原本没头没脑的话成为可理喻的,我们就必须引进情境(situation)这个概念,引进情境的结果不仅是使沟通行为得以成立,更主要的是,它使一个独白变成了对话,使原本是以言表意的行为成为了以言行事的行为,让我们设想如下的场景:
场景1:天气很凉,我走进屋说“窗子开着呢”,这时候我的意思是最好把窗子关上,这显然是以言行事的范例;
场景2:天气很热,你想开空调,可是这时我说了一句“窗子开着呢”,这时候我的意思也许是“窗子开着,如果你要开空调,先关上它。”也许是“窗子开着,已经够凉的了,就不用开空调了”,具体意思是什么,想导致的以言行事行为是什么,全凭当时的语境、对话双方的共同背景、以及听者对这句“窗子开着呢”所具有的字面意思和隐含意思的理解所决定,这里虽然没有一定之规,但也绝非可以进行任意诠释——它是有具体的规定性在里头的,换言之,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约定俗成的“义务”——义务这个字眼太强,我更愿意说成是“习惯反应”。这种“习惯反应”的力量不是来自外在规范的强制约束,而是日常语言。
事实上,对这个场景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构想:假定对话双方是一对夫妻,丈夫是说话者,妻子是听者,丈夫生性节俭,一向主张尽量少用空调以节约用电,两人此前曾为此多次口角,因此当丈夫走进房间说“窗子开着呢!”,此时就不仅意味着“窗子开着,已经够凉的了,就不用开空调了”,而且还有通过这个言语行为谴责乃至激怒妻子的意思在其中:“你怎么又在浪费电?”——很显然这是一个以言取效的言语行为,而且在这个特定的情境里面,我们可以预见到随之而来的“习惯反应”:夫妻再次大吵一顿。
以上分析表明某些言语行为后面的确伴随着约定俗成的结果,但却无法证明只有以言行事行为才具有这种约定俗成的结果;不仅如此,以上分析还证明了奥斯汀本人的一个困惑,即所谓以言表意、以言行事、以言取效的区分也许只是出于方法论上的方便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尽管在概念(逻辑)层面上我们可以勉强加以区分,但是落实到经验层面,尤其是日常对话中,这三种言语行为方式合为一体的例子却是比比皆是。可是沟通理性要想获得与工具理性对等的地位,就必须确保在逻辑层次和经验层次上的双重稳定性。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句简单的“窗子开着呢”,既可以是以言表意,也可以是以言行事甚至是以言取效行为,遑论其他更为复杂的日常对话?
哈贝马斯也许会反驳说,以言行事的结果和言语行动之间存在的“约定俗成”的关系是一种内在的关系,而以言取效行为的后果和所表达的意义的关系却是外在的,一个言语行为的可能的以言取效后果取决于偶然的脉络,而不是如以言行事那样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18]譬如上述例子中夫妻之间因为“窗子开着呢”这句话而发生的争执就是在“偶然”脉络之下发生的后果。对此,我的回答是,既然我们都认同“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则脉络或者情境的引进就是无法避免的。而脉络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着 “非普遍必然”也即“偶然”的意味在其中。事实上,哈贝马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模棱两可的态度,在《沟通行动理论》第二部中他引入生活世界作为沟通行动的补足概念,恰恰表明了这一点。在经验语用学中,不仅脉络和情境是达成理解的必要因素,说话者的“意图”同样如此。否则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在一个以言行事行为里,说话者只要求听者理解这个言语行为明白晓畅的内容,他没有任何超出内容意义以外的企图”,就是从语用学向语义学的倒退。
虽然这一点对于哈贝马斯的整体理论并不一定构成致命伤害,但不能不动摇其语用学基础的可信度。
可是哈贝马斯的工作却不仅是要指出沟通行动的独立性,他更要指出沟通行动(相对于策略行动)是更为源初和优先的言语行动。如前所述,哈贝马斯认为 “在语言使用中,达到理解是源初的模式,而在此基础上的非直接理解以及对语言的工具化使用则是寄生的产物。”[19]哈贝马斯的论证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听者无法理解说话者的意思,则这个有着策略性目的的说话者就无法让这个听者按其所愿望的方式行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那种“以结果为导向的语言使用”并不是语言的源初使用,而是包含在以言行事的言语行为之中。[20]这个论证相当简单,不过也非常有力,我们的确无法想象,如果听者连“窗子开着呢”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甚么都未曾理解,怎么可能会有其后关窗子等等一系列的结果性反应。所以当哈贝马斯因此得出结论说策略行动(所谓非直接理解以及对语言的工具化使用)是沟通行动的寄生产物时,也并非没有道理。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考虑,是不是可以得出几乎相反的结论:以达到理解为目的的沟通行动是策略行动的功能性的结构组成因素。作为目的性的动物,人们在日常交往过程中,不只是为了理解而沟通,我们之所以要达成理解,正是因为我们需要通过理解来达成理解之外的其它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沟通行动不仅难以作为一个自足的言语行动存在,而且作为一种功能性因素附属于策略/目的行动,即使我们能够将其从策略行动中剥离出来,其稳定性也令人担忧,我甚至会认为它随时有滑落到策略行动的可能。换言之,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沟通行为的发生缺乏充足的动机资源,哈贝马斯始终没有说明,在后形而上学时代中,人们通过沟通行动追求的究竟是自我利益、他人利益、群体利益,抑或是什么利益都不追求,只是纯粹的坐而论道,以知识性的相互理解和道德性的相互关怀为目标?有趣的是,在《沟通行动理论》第一卷第101页处,哈贝马斯说过另外一番话:“语言是为理解而服务的沟通行动的媒介,可是行动者与他人达成一致理解是为了协调他们彼此的行动,为了追求他们特殊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目的性的结构是所有行动概念的基础。”[21]这段话显示出哈贝马斯本人对沟通行动独立性地位的摇摆态度。看来不仅沟通行动和策略行动的区分有待进一步的澄清,而且退一步说,即使承认沟通行动和策略行动之间界限分明,它们二者谁更源初在哈贝马斯这里也是语多含糊。
第三,哈贝马斯的言语行动理论及其对塞尔的批评主要根据三个世界的划分,可是这三个世界的划分同样存在问题。哈贝马斯将世界划分为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对应于这三个世界有三种有效性宣称:真诚性,真理性和正当性。这是一种类似本体论预设的假定,然而自始至终哈贝马斯没有给出可信服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这些假定是普遍的。汤姆逊对此就曾提出批评,并指出我们可以给出其它一些别的假设,其普遍性和哈贝马斯的一样,比如前期维特根斯坦就强调过以下两种区分:1,可说与不可说的区分;2,由模态逻辑发展导致的区分,即是什么与可能是什么之间的区分。[22]
最后,哈贝马斯关于命令的言语行为分类同样存在不妥之处。在谈到银行劫犯用枪指着银行职员说“举起手来”这个例子时,哈贝马斯后来写道:“我的错误在于把这种纯粹由权力支持的有限的命令式例子作为言语行为本身。但正如齐默曼(Zimmerman)、图根哈特(Tugendhat)和斯克杰(Skjei)所指出的,我陷入了矛盾之中。我已经在回复斯克杰的时候修正了我的立场:我现在把简单的或者非权威规范的例子作为附带的例子。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我应该知晓在仅仅是作为事实的权力和已经被转化为规范权威性的权力之间存在的连续性。出于这个理由,所有具有以言行事力量的命令都能根据规范权威的命令的模式来分析。我之前在概念上所做的错误区分现在已经缩减成程度上的区分。”[23]
哈贝马斯的形式语用学及沟通行动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道德意识和伦理规范的宗教-形而上学基础丧失的背景下,如何重建我们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规范?哈贝马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但是正如威廉斯•奥斯维特所指出的,事实似乎不像哈贝马斯想象的那么清楚简单。[24]但无论如何,哈贝马斯学术气魄之宏大壮观,其理念抱负之高远坚韧让人叹服,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后现办理论盛嚣尘上的时代,哈贝马斯依然固守启蒙主义大纛,坚持人类理性的力量,可以说捍卫了人类理性最后的尊严。
推荐期刊:逻辑学研究创刊于2008年,是中山大学和中国逻辑学会主办,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承办的学术刊物,旨在积极推动我国逻辑学及相关学科的学术研究水平,增进海内外逻辑学及相关领域学术同行的交流。
SCI论文
- 2024-02-26SCI论文是全文收录吗
- 2024-08-16三类及以上期刊是什么
- 2024-07-17sci一区论文可以保研吗
SSCI论文
- 2023-11-1140本人力资源管理方向的ssci期刊
- 2023-04-07公共管理方向可以发ssci刊物吗
- 2023-06-14发ssci论文能查到吗查询流程
EI论文
- 2023-08-22计算机方向被ei检索的会议多吗
- 2023-03-28EI收录的都是英文期刊吗
- 2023-10-13ei论文查重高怎么降低
SCOPUS
- 2023-12-25艺术教育论文可以发到scopus吗
- 2023-03-08ssci期刊和scopus期刊有交叉吗
- 2023-06-16scopus检索流程(方法)
翻译润色
- 2023-05-11生物医学sci论文润色有用吗
- 2024-08-16国际中文期刊发表论文应该用什么
- 2024-08-17英文论文怎么降重
期刊知识
- 2020-12-26能源领域学术期刊影响力大的期刊
- 2022-02-18有机材料相关论文发英文普刊能用
- 2022-10-09环境类英文期刊选择方法
发表指导
- 2020-03-06肾脏病学统计源核心期刊有哪些
- 2020-07-22农艺师评高级有什么要求条件
- 2019-04-16论文审稿过程中能催稿吗如何催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