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图书分类探索中的中文古籍处置问题
时间:2019年10月16日 分类:文学论文 次数:
摘要:民国时期学界在探索图书分类过程中,普遍在杜威十进制分类法的基础上,结合中文古籍的特点,或增补加入新的类目,或采用其体系进行全新的改变。在各大图书馆具体操作时所使用的分类法五花八门,大致可分为中西文文献分开还是统一处置两种不同的方法。
民国时期图书分类探索均以杜威法为蓝本,是学界得以广泛交流的基础。民国时期图书分类探索看似成果甚多,但实际上新旧书籍究竟如何处置的问题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学界中人各自为政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变,制定出一部全国统一的分类法的目标也一直没有实现,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学界对图书分类的基础理论忽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民国时期;图书分类探索;中文古籍处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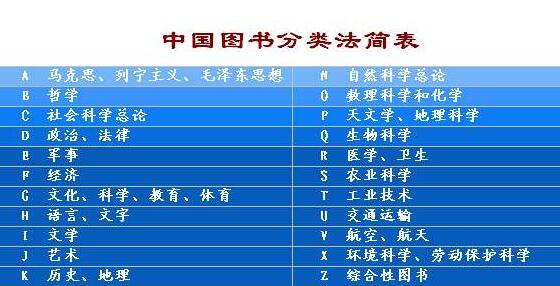
自20世纪初美国杜威十进制分类法等西方图书分类法传入中国以来,我国图书分类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动,各种类型的图书分类法在20世纪20-30年代应运而生。学界在探索图书分类方法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如何处置传统中国古籍的问题。
有关民国时期图书分类法的研究,学界更多关注的是一些图书馆学家为此做出的贡献,但与之相关的中文古籍处置方法的比较研究,则大多语焉不详。本文将在梳理民国时期图书分类法探索中各种分类方法在处置中文古籍的原则与方法的基础上,来分析不同方法之间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对处置方法总体上做出一定的评价。
一、图书分类法探索中的各种中文古籍分类方法
我国传统藏书楼时代形成了独有的、且运行长达数百年之久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方法,但自近代以来面对外来学科知识体系的新式图书,传统四部分类方法感到力不从心。从20世纪初开始各地在创办新式图书馆时,工作人员面临的首要难题,便是中西文文献能否在一个统一分类标准之下进行分类,以及如果能的话如何进行分类的问题。首先开始对图书分类法展开探索的是古越藏书楼的创办者徐树兰。
“其事集议于庚子,告成于癸卯”[1]的古越藏书楼,是由绍兴缙绅、著名藏书家徐树兰先生创办的。徐氏抱着“存古开新”的宗旨,除了搜集不少古籍善本外,还收集了不少新学之书。他在编写《古越藏书楼书目》时,将所有图书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之外,增加“时务”一部,并将之分为学、政两大类。
古越藏书楼分类法打破了传统四部分类法的分类体系,将以往四部没有涵盖的学科一并划分到学部或政部之下。作为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界在图书分类方法探索中的第一次尝试,古越藏书楼分类法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继古越藏书楼分类法之后出现的是孙毓修编制的分类法,孙氏也是最早撰文向国人介绍杜威十进制分类法的学人。
1909年,他在《教育杂志》“名家著述”栏目中连载《图书馆》一文,首次向国人介绍了此分类法。孙毓修认为:“新书分类,断不能比附旧书联为一集者,以其统系至广且博,非四部之界所能强合也。惟事方草创,前乏师承,适当为难耳。”[2]他在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基础上“量为变通”:将欧美通行的类别进行变通分为22部,用于新学之书的分类。
虽然该分类法还没有类号,但是已经借鉴了欧美分类法的一些优点,例如差不多在每个大部下,都先设总记类,其下再设字书、学史等小类,反映出孙毓修已经基本掌握了分类法的编制原理和体系结构。他提出对新旧图书进行不同的分类方法:即旧书仍然依照传统的四库法,而新书则依照自编分类法。
孙氏所编制的新旧并行制分类法一经提出,响应者一时蜂起,如当时的江苏省立图书馆、浙江省立图书馆起初均采用此种方法进行图书分类。古越藏书楼分类法和孙毓修的新书分类法,被近代图书馆学家蒋元卿称为编制新法以容纳新旧图书的开创和新旧并行制的一大创举[3](P.157-159)。这两种分类法代表了在以杜威分类法为代表的西方分类法尚未在国内产生重大影响之前,中国图书馆学界对图书分类探索的成就。
它们是基于当时图书馆藏书的实际状况和人们对于知识体系的认识,而提出的切实可行的图书分类方案。尽管这些分类法还有着很大的弊端,但作为国人对分类法的早期探索成果仍然是值得肯定的。新旧并行制虽然解了起初图书分类的燃眉之急,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接采用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又不符合中国国情,随后打破这一僵局的是沈祖荣与胡庆生。
沈、胡二人鉴于“现在各国图书馆大形发达,出版之书,日新月异,浩如炯海,繁如牛毛,即《杜威十类法》,善则善矣,如谓毫发无遗,恐难自信。即以美洲而论,图书馆用《杜威法》,迄今颇觉困难”的现实情形,于1917年编制了《仿杜威十进分类法》,起初命名为《中国书目十类法》,后来称之为《仿杜威书目十类法》,于1922年由武昌文华公书林正式发行。二人在编制该分类法时“不必拘专与杜威相吻合,惟期适用而已。”[4]
他们将杜威原著的“总类”改为经部及类书,将哲学宗教、语言与文学合并,增加政法与经济和医学类目,开创了将所有新旧图书融为一炉进行分类的先河。由于《仿杜威书目十类法》是我国最早仿效杜威十进分类法并“参以己见”而编制的图书分类法,“既系开山之书,较之近人著作,自为简略,然其所设类名,后之师之者,颇不乏人。”[3](P.207)
此后的20世纪20-30年代学界对图书分类法的探讨成果层出不穷,基本上都是根据杜威十进制分类法的基础上编制,同时也参照沈、胡二氏编制的分类法,先后涌现出的图书分类法有数十种之多。这些图书分类法大致可分为增改派与采用派两大派别。就增改派而言,他们只是在杜威十进分类法基础上更改条目,保留了其分类原则。沈祖荣与胡庆生编制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无疑是增改派的鼻祖。
在随后的增改派中,刘国钧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编订的《中国图书分类法》于1929年由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印行初版,1936年增订再版。在类表编制过程中,刘国钧采用了新旧分开编制类目的办法。“关于中国固有之类目,则大率采自汉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文献通考经籍典、张之洞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
他将所有经史子集文献分别归于不同的类别,如经部归于总部的丛书一类,史部归于史地类,子部与集部因为较为杂乱,故分别归于不同的类别。对于新出现的学科,“则采自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者为最多,而杜威十进分类法次之,布朗、克特两氏之分类法亦多资参考。”[5]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对此后中国图书分类法的发展影响深远,在实践中也为许多图书馆所采用。与增改派不同的是,采用派则基本上只是利用了杜威十进制分类法的体例,对十进制分类条目进行了重新调整。
“虽亦用杜法分为十类或九类,然其所立类目,大都不与杜法相同,而系采其十分符号而已。”[3](P.226)最早开始采用杜威十进制分类法体例来进行分类法创造的,当以1924年洪有丰为国立东南大学孟芳图书馆编制的《孟芳图书馆图书目录》为首创。洪氏在其序言中曰:“今日中国各图书馆于编制中文书目,有新旧之聚讼,莫衷一是。经史子集四部之旧分类法,于近日科学图书日益增加,诚有未能应用之处,然为之改弦更张以科学分类法自诩者,袭摹西制,支离繁琐,强客观之书籍,以从主观之臆说,恐亦未免有削足适履之嫌。”[6]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洪氏依据四库全书总目,并在参酌杜威十进制分类法的基础上,将所有新旧图书分为丛、经、史地、哲学、宗教、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艺术九类。在这九大类中,丛类与杜威十进制分类法的总类相似。经类与四库全书分类法大体相同。儒、墨、名等各家性质与哲学相近者以哲学名之,分为东方与西方哲学二目,宗教因与哲学关系密切亦并入该类。
因法家与纵横家多论政法,归入于社会科学类。“社会科学以下各类,均参酌杜威氏分类法。惟遇细目不适用于中籍者,则加私意增删,或改易之。非敢臆造,期适合于中文图书之性质也。”[7]自洪有丰开创采用杜威分类法原则之后,受此影响出现的采用派分类法为数不少。且采用派后来在海外亦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裘开明根据他所工作的哈佛大学汉和文库的需要而编制的哈佛大学中国图书分类法。
国内采用此种分类法的是与之有着密切业务往来的燕京大学图书馆。该分类法采用“以中法为经,西法为纬”。整个分类法大纲编制是“根据魏荀助新簿经子史集及清张之洞书目答问别立丛书之次序”,将之扩充为经学类、哲学宗教类、史地类、社会科学类、语言文学类、美术类、自然科学类、农林工艺类与总记类等九大类,“每类子目则参考四库成法,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及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定订之。”[8]
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裘开明编制的分类法是为了适合哈佛燕京学社汉和文库收藏大量中文古籍图书的需要而来,因之与洪有丰的分类法又有所不同。简而言之,民国时期学界在探索图书分类时,对中文古籍的处置原则有共通之处。
从理论层面来看,他们均希望打破以孙毓修为代表的新旧并行制的做法,将中文古籍与新书以及西方书籍纳入一个分类标准之下来进行分类作业。有所不同的是,增改派是将中文古籍纳入到杜威十进制体系之中,在此基础上增加新的条目来容纳中文古籍。而采用派则直接打破了杜威十进制分类体系,将中文古籍按照性质的不同,分别纳入不同的学科体系之中。不过各地图书馆在实际操作时,却并非按照这样的理念进行。
二、中文古籍处置方法的异同与利用情况
民国时期学人们对图书分类的探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不过这些五花八门的分类法在各大图书馆的应用情况却区别很大。在各大图书馆实际运行过程中,对中文古籍分类的处置方法差别更大。大致说来,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将中文古籍与所有新式书籍分开处置,旧书采用传统的四部法,新书采用最新的分类法,亦即新旧混合制;另一种则是将馆藏所有图书均按照一个统一的分类方法来进行处置,亦即中外统一制。
首先,有相当多的图书馆仍旧采用的是新旧混合制来处理图书分类问题,其中尤以各种综合性图书馆为盛。由于这些图书馆先前所收藏古籍较多,故对之仍然延续过去的四库分类法;而对新书则采用新式分类法进行分类。如国立北平图书馆“所有中文图书大致依四库分类法体例而略加变通分为经史子集及汇刻五大类,仍各分别子目善本书目。
西文书目分类在欧美已有成规自可择善而从,本馆西文分类系采用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以其颇适用于大图书馆之收藏。”[9]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国立中央图书馆。该馆在筹备过程中,“参合各家分类法,略加改订,类别务求精确,细目务求详尽,庶同码之书,不致重见叠出。西文书籍,现尚无多,似无另立分类法之必要,故暂采用美国国会图书馆之分类法。”[10]一些地方图书馆的情况与国立图书馆情况相类似。
如安徽省立图书馆在新书分类法的选择上,“系根据杜威十进分类法,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略加增损。”[11]起初该馆分类法一概从简,后因新书日渐增多,过去所定类目,颇不敷用,因此又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目中的分类表与国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类目,以供该馆之用。
其次,各大学图书馆在图书分类实践中,则与综合性图书馆有所不同。由于此时正是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各大学在办学过程中普遍采用的是与西方接轨的做法,因之无论是教材还是参考书均以西文文献为主。如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对中日文图书与西文图书采用基本相同的分类方法,中日文书籍采用最新的中国十进分类法,西文图书采用杜威分类法[12]。清华学校图书馆1923年才开始正式进行图书分类编目工作。
起初该馆因中西文图书的性质不同,将之分为中西两部,实行的是新旧混合制:西文图书分类釆用杜威分类法,而中文书籍则又以1923年为分界线分为新旧二类。旧书采用经史子集丛五门分类;新书则仿杜威十进法分为十门而稍加变通。自1923年以后,该馆废除新旧混合制,所有书籍全部采用杜威法分类的基础上增补其他类目。
1927年,洪有丰出任该校图书馆主任后,在他的主持下采用了新的图书分类法进行分类。1929年以后,该馆“因书数大增,旧法不适于用,分类益感困难,乃参酌中外各分类法,从事改编,并将草案分请校内外专家,予以审定。是表计分八大类,八千小类。”[13]自次年起,该馆中所有没有编目的中日文图书,均照新的分类法进行分类编目。
据1934年蒋元卿先生的统计,当时除了极少数图书馆仍旧采用的是在四部分类法基础上略加变通,或者是四部分类法与杜威分类法相结合之外,大多数图书馆采用的是新旧混合制的分类方法:即中文图书大多采用国人新编制的分类法,西文图书大多采用的是杜威十进制分类法(也有少部分采用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
也有相当一部分图书馆采用统一的标准将所有馆藏中外文图书统一分类,如在蒋元卿调查的图书馆中,有7家使用的是杜定友的1922年编制的《世界分类法》,有8家使用的是王云五1924年编制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使用杜威十进制分类法的图书馆更是高达12家。使用中外文图书统一分类的图书馆基本上形成了杜定友法、王云五法与杜威法三分天下的局面[3](P.259-264)。在中外文图书统一分类方法的理论探索中,以杜定友与王云五所开创的分类法最具代表性,也是引起学界争论最多的两部分类法。
杜定友坚持“聚中西贤哲于一堂,汇古今文化于一室”的理念,希望将所有图书采用一种统一的分类标准,因之编写了《世界图书分类法》,1922年首先由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出版。与杜定友的《世界图书分类法》相类似,王云五创设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同样主张应该采用统一的分类方法对所有馆藏图书进行分类。
他认为,杜威的十进分类法可繁可简,排列顺序基本上符合于学术研究工作,是最适用于中国的分类法,但对于中国传统古籍却仍然无所适从。他从街道小巷编门牌的办法中得到启发,自行创设为中国图书特增的类号“+”号,以别于杜威的原类号,同时杜威的原类号还是一点没有变动。在此“+”号的基础上,再扩充为“+”、“卄”与“±”三种附加符号,用以表示中国特色的书籍,排在杜威十进分类法相当或有关号码前面,与原有号码先后排列[14]。
这样不仅分类法可以不断增加新的内容,而且还可以兼收中国传统经史子集等图书。以上两种分类法更多的是要解决中国传统古籍如何与新书在一个标准下进行分类的问题,是中西融通的大胆创新。杜定友的《世界图书分类法》出版之后,学界对之提出一些疑问,主要包含三个层面:首先,将新旧图书一并改为十分法后,一般旧学者会难以检查。对此杜定友回应称:“盖从前我国图书馆学与目录学者,只知有分类目录,而不知有其他目录。
故欲检查书籍,则非熟念分类方法不可。不知现在之图书目录,有书名著者种类各种,故不患不易检查。”其次,针对中西书籍装订不同,并列在书架上一横一竖不太雅观,故在装订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中西文图书不能不分别贮藏。杜氏认为分别贮藏,用数字与字母分别标注著者号码,“故二者判然可别”。
最后,将西文与中文新籍图书并藏,而将旧籍分贮则类码或书目必须更改的问题,杜氏亦认为没有问题,“盖世界图书分类法实已将四库法包含在内。不过彼则经史子集,此则经子集史而已。”[15]对于王云五开创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出版后,武汉大学杨端六教授对之评价甚高,认为“他把中国字变成号码,并且把西文字母也变做号码,所以对于著作人的姓名有了一个统一的办法。不过中外图书的统一,并不是很难的事。
因为无论什么图书,中文也好,西文也好,日文也好,总要给它编一个号码。这个号码就是一个天然的统一法。用不着再有一个号码。”[16]不过著名的图书馆学家金敏甫对之评价不高,认为该分类法除了增加了“+”、“卄”与“±”三种附加符号外,“全是杜威氏的原著,而且就大体上论,依然是杜威分类法。”[17]金氏之所以对王云五的分类法评价不高,是因为该分类法从理论建树上来说似乎不高。
但图书分类法更多讲求的是实用性,王云五的分类法在很多图书馆大受欢迎,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国时期图书分类探索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些距离。
三、民国时期中文古籍图书分类与处置办法的总体评价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界在对图书分类法探索过程中的成就非常丰富,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分类法值得高度肯定。这些分类法基本上都是在杜威十进制分类法的基础上改进而来,因而为学界有关图书分类法探讨过程中的对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对于如何处置中文古籍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其中四部的经部究竟应该是分开还是合并处置的问题尤为突出。
正如蒋元卿在1937年所指出的那样:“经部分合,已成为近代分类法上一大问题。二十年来,迄无适当办法。洪氏所说:‘尚待于研究’一语,不为无见。”[3](P.251)之所以出现此种局面,既有表面上学界中人各自为政的原因,也与学界普遍忽略图书分类基础理论的探索等多方面的因素有关。民国时期学界探索图书分类最终没有很好解决中文古籍的处置问题,是学界基本上是各自为战的必然结果。
早在20世纪20年代,吴敬轩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曾提出一个全新的分类方案:即依照“现代图书分类法”来定分类编目,将所有古籍拆分为单行本来分类,但实际操作过程中他发现有两大问题亟待解决:一是“书籍内容含混,不易辨别”;二是“中国书籍浩如渊海,每一部书里面,往往含有分类法中四五种门目以上,如果一一去分析起来,纵合十人之力,恐怕十年也还闹不清楚。”
因此吴氏提出:“最好是能组织一种具体的机关,如图书分类局之类,由国家或地方公众担任长期的经费,网罗海内硕学通人,担任这种伟大的文化事业。”[18]刘国钧在此后不久亦表达了学界合作编制分类法的愿望。他说:“夫图书分类其事至难,欲凭一人之力,势必无所成就。故莫如集多人而研究之。
然图书分类又非空言所能有济。是以各当以其实地之经验,互相告诉,以便修改。质言之,即合作两字而已。”他还表示组建此类组织的目的,“在促进使用此种发来的者之互相研究。如有疑难之点,得由众解决之。如以人有修正或横充之处,宜即通知各员,请其采用或供其参考。如此则有较完美之分类法出现也。”[19]
学界也曾经意识到图书分类工作的重要性,希望实现学界力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图书分类事业的发展。早在1925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之初,就设立了分类委员会、编目委员会与索引委员会,着手加强对图书分类与编目的研究工作。在1929年召开的协会第一次年会上,分类编目组明确提出由分类委员会编制分类法案,并由大会议决供委员会采择之规定分类原则四项。鉴于分类法是各图书馆开展工作的必须标准则,分类委员会对“一切所创制之中籍分类法”广泛征集,并征求各馆对已刊行分类法的使用意见,以备参议。
在第一次年会召开过程中,分类编目组曾召开了三次会议,第一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图书分类问题,金敏甫提出了《厘定分类制度及编目规则案》等10多个提案,决议规定分类原则:“一是中西分类一致,二是以创造为原则,三是分类标记需易写易记易识易明,四是须合中国图书情形。”[20]为了此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协会还在次年发布公告,“特为广征一切所创制之中籍分类法,如用四库或已刊行之分类法,则亦请示知其效用及可以商榷之点,以备参考。”[21]
结语
自杜威十进制分类法进入中国以来,学界在探索图书分类时均以之为蓝本,先后涌现出的分类法有数十种之多。所有这些分类法在处置中文古籍时,均面临着究竟是将之单独处理还是将之拆分适应外来学科分类的问题。虽然涌现出的分类法数量达数十种之多,但究竟中文古籍如何处置的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是学界之间的合作太少,基本上还是处于各说各话的阶段,学界同仁所希望的创立一部全国统一的图书分类法的梦想也一直没有实现。虽然学界中人也认识到了此种缺陷,作为全国性学界团体中华图书馆协会也曾努力想开创新的局面,但最终目标一直没有实现。
总体看来民国时期学界对图书分类的探索过程中受美国杜威十进制分类法的影响太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学界囿于该分类法无法自拔,对西方其他类型分类法的借鉴利用不够。再加上学界普遍对图书分类基础理论的重视程度严重不足,对可能会影响到图书分类探讨的其他学科发展的关注尤为不够。此外,学界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也较为欠缺(唯一的亮点是特殊的历史机缘,造就了裘开明主持哈佛大学汉和文库所开创的分类法)。所有这些遗憾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图书馆从业者评职论文范文:国家图书馆新闻宣传工作如何有效开展
近年来,全民阅读推广已经成为图书馆一项重要工作,国家图书馆尤为重视新闻宣传在推进全民阅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为此下面文章在国家图书馆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大型展览、世界读书日、重大文化工程方面的新闻宣传实践基础上,对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思考,提出要制定宣传方案、构建新闻宣传平台、成立专门宣传机构、组建宣传志愿者队伍。
SCI论文
- 2023-08-01sci四区发论文最容易吗
- 2023-05-10英文论文的检索号是什么
- 2024-10-23SCI期刊要自己推荐审稿人 推荐谁
SSCI论文
- 2024-02-02学霸笔记:超级好用的ssci论文发
- 2023-03-08全球经济趋势分析论文发表ssci期
- 2024-03-22SSCI四区的文学期刊
EI论文
- 2022-08-12发表scopus论文的步骤
- 2022-11-11ei会议论文会拒稿吗
- 2023-05-31纺织类的ei期刊(3-5本)
SCOPUS
- 2023-03-14scopus期刊收研究生论文吗
- 2023-02-20scopus检索与ei哪个好
- 2023-04-21论文被scopus成功录用需要多长时
翻译润色
- 2023-05-06基因测序文章怎么翻译润色
- 2022-05-07sci论文润色更容易录用吗
- 2024-08-17国际中文期刊评职称承认吗
期刊知识
- 2021-01-16高钾血症论文发表期刊
- 2020-02-07sci期刊发表的论文都可以被web o
- 2022-03-08火电厂论文外文翻译有什么服务
发表指导
- 2024-08-17氧菌论文可以投稿的期刊
- 2018-04-04经济学动态发表论文审稿周期多久
- 2021-08-07电熔炉相关论文文献看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