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媒介的“街头诗”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学传播的情感动员
时间:2021年09月29日 分类:文学论文 次数:
【摘要】对人民群众的情感动员在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抗日战争中作用卓著。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以街头诗为代表的文学传播媒介发挥了重要的情感动员作用,从媒介生态学视角出发,在根据地的特殊社会历史语境中,街头诗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在时空、文化、政治方面的媒介偏向是决定其情感动员效能的重要因素,通过构建集体认同—情感对话—意义共享的情感动员逻辑,实现了多媒介联动式传播与情感动员网络的构建; 依托社会组织,嵌入根据地的己群社会关系,在圈层式传播中进行情感动员; 从政治动员下沉到文化自觉,建构了集体协作式的革命情感传播路径。 街头诗媒介的情感动员在全民族抗战的目标指引下,转化为政治的共意动员,实现了对根据地军民群众的精神教育和审美教化,促进了反思性、成长性的国民身份转向与形成。
【关键词】晋察冀 媒介生态学 情感动员 街头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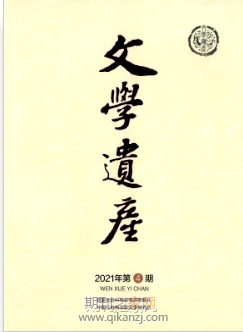
情感是人类行为活动的发动机和内驱力,中国历史中的革命主体历来重视情感在推动革命实践中的作用。 现代实证主义的史学研究中,整合传统的制度研究和民族文化、心态或气质层面研究的转向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其中,情感史研究以探究革命过程中人的情感表达、心灵与情绪、精神气质及其与革命实践、传统文明的互动机制为目标,对以往以政治结构、军事力量、阶级斗争为阐释框架的革命史研究进行了必要且有益的补充,为中国革命研究打开了新的空间和维度。 [1]在情感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研究对象便是情感在革命动员中发挥的突出作用即情感动员,指的是“个体或群体通过情感表达,在持续的互动中唤起、激发或者改变对方个体或群体对事物的认知态度和评价的过程”。 [2]
文学人员评职知识: 文学遗产期刊投稿要求
媒介生态学科的设计师克里斯琴·尼斯特洛姆认为,语言应被作为最重要的媒介来研究,语言及一切表征经验的符号系统影响我们如何构建现实。 [3]从媒介生态学视角出发,文学作为一种最为典型的以表达情感为目的的语言传播媒介,其传播过程参与了社会革命中情感动员体系的构建,文学活动与传播活动交叉互动的平台也是媒介,媒介的形态特征必然会影响其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和整体面貌。 [4]将文学传播置于媒介生态学中进行考察,是揭示其媒介属性、剖析文化发展本质的一把秘钥,只有将文学本身作为一种媒介形式进行考察,才能深入理解其情感社会动员效能及其所建构的社会实践。
抗日战争中,为广泛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革命根据地并动员群众力量成为历史性选择。 战时情境下,街头诗作为一种新型传播媒介兴起于延安,后传至晋察冀边区并逐步扩散,成为根据地文学传播大众化的重要标志。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继延安之后街头诗运动开展得最早、最活跃且成绩最为突出的地区。 [5]创作者将短小精悍、朗朗上口的诗歌题写在墙、门窗、岩石、交通要道口甚至枪杆等日常媒介物上,以达到即传即达的效果,以“鼓动性的韵律语言”表现出“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的情感动员。 [6]可见,街头诗作为一种传播媒介,自产生起就伴随着情感动员的功能。 其在抗战革命历史中发挥着安排、组织、转化与再造情感的社会功能,体现了特殊历史语境下党对文学媒介工具及其情感动员功能的科学认识和宏观把握。
一、作为媒介的街头诗:媒介偏向与情感动员
媒介生态学的传播偏向理论是分析媒介对于文化影响的重要路径。 按伊尼斯的说法,偏向是指某种技术带来的文化倾向,不同技术带来不同的文化倾向,[7]使用媒介偏向分析法可认识到“古今各种媒介的作用与反作用”,让人们看到媒介“所处历史阶段社会制度的构建”。 [8]从媒介生态学的视角来看,街头诗媒介的物质和符号形态构建了其相应偏向的时空的、知觉的、文化的、社会的媒介信息场域,使之成为抗战根据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动员受众情感的特定传播媒介。
1. 时空偏向:媒介载体特征与情感动员效率
从媒介时空偏向而言,街头诗的媒介载体在传播层面的特殊性凸显:从空间维度来看,不同于文学刊物、书籍等以纸张为载体的媒介,街头诗主要依赖于自然物或建筑物等非流动性载体,突破了根据地纸张短缺、印刷困难的条件限制,使媒介内容得以随地、随处传播,同时也使得以往的流动性、主动性传播方式,如各地分发、渠道贩卖等过程不复存在,“固定化媒介、流动性受众”的传播方式缩短了传播流程,提升了媒介内容在空间上的情感动员效率; 从时间维度来看,与文学改编的戏剧表演等媒介不同,街头诗的物质载体质地较重、耐久性较强,一方面可长时间保存,时间的障碍因而被克服,[9]另一方面媒介内容的历时性使之实现了对受众的复次传播,并不断巩固情感传播效果,其对生活场景的嵌入,更易将受众印象转化为记忆产品,从而潜移默化地对受众情感施加影响。 街头诗在传播广度、深度上的显著优势得到凸显,其编制的时空传播网络为其在技术条件欠缺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广泛动员抗日情绪、在时间紧迫的战时情境中高效率地凝聚受众情感,提供了媒介条件。
2. 文化偏向:嵌入日常的媒介仪式与情感动员的扩展
晋察冀的特殊地理环境塑造了其相对固守、封闭的群体意识,一定程度上为媒介的情感动员造成阻碍。 罗森布勒认为,对特定媒介的使用成为一种规则时,“带有仪式表现形式的媒介化的传播”便会形成。 [10]在根据地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街头诗的传播建构了一种潜移默化的规则性表演模式,持久性、广泛性、表演性的媒介仪式与受众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推进着情感动员的扩展。 具体表现为,在形式上须富有音乐性和节奏感,其接受过程通常“是从节奏(一般是从段式、韵式)开始”,偏重协调性与一致性的外在表演形态。 [11]另外,在1940年后还衍生出诗配画的展演模式,如田间的街头配画诗《坚壁》,与美术结合的传播形式蔚然成风。 诗人们“用自己的手,用自己的口,把自己写出来的诗歌,直接地、迅速地写在街头,在大会上朗读”,[12]由此形成了创作—抄写—读诗的仪式流程。 詹姆斯·W.凯瑞认为,传播不是信息的传递,而是文化的共享。 [13]街头诗以其音乐性和文学性结合、现场书写、书画结合、公开朗诵等符号性、象征性展演构建了文化共享的传播仪式,带动了包括农民、学生、勤务员等根据地群众广泛参与、自发创作街头诗的热潮,在乡村社会圈层式的人际社交中实现了参与性、公共性的媒介仪式的生成,联结与维系了扎根于传统、激发于革命的集体主义信仰,为实现情感动员的扩展奠定了社会心态基础。
3. 政治偏向:媒介舆论空间的建构与情感动员的深入
情感动员想要真正取得效果,除传播广度外,提升受众对传播内容的认知程度尤为重要。 在晋察冀根据地受众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人民联系紧密且公共性媒介活动甚少的社会情境下,建构以意见领袖为主导的公共舆论空间成为情感动员的有效途径。 街头诗写上墙后,有人就地朗诵给群众听,创作者将街头诗公开后,以识字的群众朗诵者即意见领袖为节点,以人际网络为轴,在根据地社区中实现传播扩散,与文字形式相配合,充分发挥宣讲、朗诵等非文字形式在舆论生成中的重要作用。 [14]街头诗人田间回忆道:“街头诗写在墙头或贴在门楼旁以后,马上便围上一群人,有手执红缨枪的,有手持纪念册的,有牵着山羊的,有嘴含大烟锅的,都在看,都在念。 ”[15]街头诗创作者“提着一缸子浆糊,把它(街头诗壁报)贴在岚县中学门口的墙上,顿时,学生们涌了出来,围在诗壁报前观看,有的边看边朗诵,有的还当场抄录”。 [16]由于朗诵以情景化的方式展开,传播者的非语言要素及声音、风貌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激发受传者的接受欲望,调动受传者的情绪,影响接受的效果。 [17]同时,在街头诗建构的媒介公共空间里,街头诗围观者即众人的意见经过群体合意形成舆论,由此动员的集体情感深入影响个体感知,改变了根据地的社会情感组织方式、人际关系乃至政治参与面貌。
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街头诗传播的情感动员逻辑
媒介生态学将媒介本身视为一种媒介环境,媒介描摹的符号形式为人们表征了一个符号世界,其形象与概念的建构依赖于人对语言符号结构及逻辑的理解能力。 [18]街头诗媒介经由各类语言叙事符号的编码建构情感动员的符号环境,并通过受众解码即理解、接受过程使情感动员机制发挥作用。
1. 塑造共同受难身份与集体认同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街头诗通过对非正义叙事框架下军民群众共同受难经验的深描,将内容生产者对现实的主体性反思外化为媒介产品,通过选择编码、意义嫁接、整合呈现等传播手段,将符合公共秩序与价值观念的个体受难情感记忆进行典型化加冕,从而为构建共同的受难身份、唤起集体认同提供了路径。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田间《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祖国,让我喊出/你的愤怒吧! /喊出你的苦! /深重的苦痛! ”——冈夫《我喊叫》
“连断砖/也流出血水/牢记这仇恨”——荒冰《轰炸吧》
街头诗作为一种媒介,通过传播受难叙事中的个体反思,激发普遍的愤怒、反抗激情,从而形成情感动员的起点与契机。 受众通过朗诵、展演、自发再创作等复次传播活动使这种激情再次发酵,并在受众群体内部进行意见交换的过程中达成认同,获得了基于共同受难身份的广泛的经验参照与社会支持。
2. 抵抗诉求与情感对话机制的建构
反映军民战斗生活的传播叙事亦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街头诗中占有重要地位。 抵抗对象即“敌人”的威胁性与抵抗主体即“我们”的主体性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不断塑造作为共同体的抵抗者身份。 对抵抗双方关系的清晰解释,构建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情感对话与双向理解,以达成说服和移情的作用,从而为街头诗情感动员的落实提供通路。
“恶狗扑人人不怕,敌人来了困死他”——冈夫《敌人来了困死他》
“我们是无敌的游击队/无敌的游击队/我们的神速赛过空中的飞机/袭击着敌人的腹和背”——高敏夫《我们是无敌的游击队》
“莫说我们是娃娃/拿着枪/骑着马/我们也要救国家”——巩廓如《少年先锋队》
与受难叙事关注受众的情绪引导不同,抵抗叙事重在提示受众认知、指引情感的流动方向,即转向反抗和斗争实践。 前者将受众置于现实的情感情境中,发挥情感导入的传播功能; 后者则将情感通向实践的路径并进行清晰描摹,通过情感导出,使情感动员的目标被进一步引向实质性行动。
3. 建构情感联结与意义共享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街头诗中,涌现出很多以关系联结为目的的传播叙事,传播者以亲近性、口语化的情感表达建构了与受众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同一性。 在情感联结的基础上,受难叙事的集体认同和抵抗叙事的情感说服转化为集体的意义共享。
“敌人已经来了,而墨斗店的一个老乡没有跑及……擦着刀,敌人狠狠地说: 我今天可刺死了一个中国人”——魏巍《一个老乡的被杀》
“老乡,你过来/咱们欢迎你/头顶上是咱们的天/脚底下是咱们的地……拉起手来哟拉起手来/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内/有权利自由呼吸”——林火《老乡,你过来》
“老乡”“中国人”等共同的身份联结在传播中被展现,传播者通过强调群体属性寻求互动与支持,同时,受众在自发的复次传播和情感共享中纾解孤立感,爱国主义、民族认同等集体价值观得以最终形成,实现了在文化、心理、认知等多个层面的广泛社会联结,情感动员的效能得以升华。
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街头诗传播的情感动员路径
媒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社会组织共同创生的意义空间是构建媒介生态系统的要素,在根据地街头诗传播过程中,多种媒介、多重情感动员模式纠合在一起,勾织出其特有的情感传播系统。 从空间层面看,党报、文学刊物、书籍等媒介与街头诗进行联动式传播,以多种媒介为传播据点,通过乡村组织扩散,实现了情感动员的协同式传播; 从时间层面看,街头诗传播的情感动员呈现以集体协作为特征、由政治动员向文化自觉过渡的大众化路径。
1. 多媒介联动式传播:根据地情感动员网络的构建
街头诗在晋察冀根据地并非以独立的传播网络和情感动员形式一以贯之,而是在与其他媒介的互动中、在多种媒介共同建构的综合传播网络中实现情感动员。
(1)党报、文学刊物等定期出版、流动发行的传播媒介,拓宽了街头诗媒介的情感动员网络,通过大众传播赋予了街头诗在传播动员领域中的合法化地位,将其受众范围由晋察冀边区群众扩展到华北地区乃至全国其他抗日根据地。 1941年至1943年,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影响最大的大区党报之一《晋察冀日报》曾发表大量曼晴、田间的街头诗,《抗战报》的文艺副刊《海燕》也不时选登街头诗作,街头诗的集合刊物《诗战线》每周出版后即送至《抗敌报》(《晋察冀日报》前身)编辑部和晋察冀通讯社,由编辑参考和选择可刊登的街头诗作品。 发表街头诗作品的还有边区的《救国报》《察哈尔日报》《冀东导报》等报纸的副刊,以及田间主编的《晋察冀文艺》《战地文艺》《文艺报》等数十种文学类报刊,[19]街头诗逐渐成为根据地典型的主流媒介。
(2)报刊宣言、新闻评论为街头诗提供了必要的顶层设计和理论指导。 关于街头诗传播的总纲性、指导性文章常被发表在晋察冀边区的《抗敌报》《抗战报》等的副刊上,为其情感动员指明方向,并总结实践经验,提出改进策略。 报刊上发表宣言是常被运用的一种形式,如街头诗人史塔发表在1938年10月26日晋察冀边区《抗战报》副刊《海燕》创刊号的《我们宣言》称:“目前,一切应服务于抗战,诗自然也不例外。 处在敌人后方的晋察冀边区,同其他地区比较,更直接处于战斗环境,因此,就更加需要诗歌工作者努力来写诗——用大众的语言写,来鼓舞战士,教育群众。 由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印刷比较困难,不用说印诗集,就是印传单也不容易,所以我们希望诗歌工作者写街头诗,开展街头诗运动。 晋察冀边区的诗歌工作者们,到街头上去! 写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 唱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 ”[20]这种宣言式报刊评论直接、有效地指导边区街头诗的情感动员方向。 另外,报刊通过发表对边区街头诗的新闻评论,为明确其动员形势提供了来源,如孙犁曾评论街头诗运动的开展状况:“这里没有数字,因为每个村庄墙头上都有了街头诗。 如果要数字,那就是边区全部的村庄、全部的墙壁。 ”[21]
(3)报刊还为街头诗开辟专页、专栏,如《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年初出版了《街头诗运动专页》,其文艺副刊《新地》也开辟了街头诗专栏,刊登了大量晋察冀街头诗作品,报刊整合化、规范化、定期出版的传播模式与街头诗流动式、分散式且富于灵活性的传播方式结合,在根据地群众的情感动员中上下呼应,优势互补。 空间维度上,报刊打破了街头诗在地域流通方面的限制,克服了其难以完整记录和保存的缺陷,以大众传播网络极大地扩展了街头诗情感动员的受众基础,而街头诗又在抗战中信息传播路径被封锁、报刊无法正常出版和发行之际继续发挥其动员作用; 时间维度上,报刊的收集、记录功能将街头诗成果保存下来,以媒介记忆的形式实现历时性的情感动员。
(4)街头诗的传播衍生出其他文学传播的媒介形式,在复次传播中不断扩大街头诗的情感动员效能。 一是出现了专门收录街头诗、油印出版的街头诗集,并在根据地广泛传播,如收录了田间、石群、力军、曼晴、魏巍、邵子南等著名街头诗人的《粮食》《文化的民众》《战士万岁》《街头》《在晋察冀》《力量》等作品,以集合性、连贯性、积累性、规模性的传播形式扩大了分散性街头诗的动员效能; 二是出现了由街头诗改编而成的抗战歌曲,配合鼓舞人心、激情轩昂的音乐与节奏及口口传唱的传播形式,使街头诗在根据地的情感动员作用进一步扩大。
2. 嵌入差序格局的圈层式传播:依托组织的情感动员模式
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指出,组织系统内意见领袖作为早期采用者,对群体获知新事物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群体中众多跟进者的态度对群体接受产生影响。 [22]晋察冀根据地以乡村传统社区为主要的传播基础结构,以己群传播为特征,[23]因而,由意见领袖发起、依托组织进行街头诗传播成为普及这一新媒介的重要策略,通过圈层式的传播方式嵌入根据地社会关系的差序格局中。
根据地街头诗的情感动员以政府和民间组织为重要节点,展开依托于组织传播的多层次、交互式、扩散式情感动员。 1939年1月,街头诗运动由军政、文化干部等组成的铁流社、延安来的西战团等诗歌团体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率先发起,随后至1939年6月,两个诗歌团体又进行过三次以街头诗创作和传播为主题的大规模合作,以组织领导为核心,街头诗运动对受众的情感动员在组织圈层中不断扩散。 据西战团的带头人田间回忆,街头诗的传播在剧社、文救会、妇救会、民众教育馆、宣传队、学校、部队甚至农会等组织中展开,并对当时街头诗汲取和反映群众的故事、感情、欲望及感情力量的经验加以强调,[24]这说明街头诗原本的大众化传播形态依托组织传播发挥作用,组织在根据地实践的情感动员中充当了关键性角色。 海燕社、铁流社、战地社、晋察冀诗会等社团组织在晋察冀地区的街头诗传播中十分活跃,其创办的街头诗刊物还送往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群众剧社、华北联大等组织,激发了组织之间的信息联动,扩大了街头诗传播的动员效应。
1940年,乡村文艺训练班创办并普及,响应街头诗运动真正与人民群众在一起的号召,广泛动员根据地群众参与街头诗创作和传播。 1941年6月,边区太行诗歌社成立,在许多部门、团体和地方的努力下,形成一支超过200人的诗歌创作队伍,各阶层、各年龄段、各社会身份的群众均有参与,可见街头诗依托组织传播达到了良好的情感动员效果,真正深入根据地群众基层。 另外,凭借组织系统,组织活动得以顺利进行,[25]根据地的街头诗还在组织活动中进行情感动员,包括动员参军、慰劳部队、欢迎战士凯旋、送战士出征,乃至做军衣军鞋、送军粮、欢迎国际友人、锄奸防特。 在具备统一管理制度、活动流程和动员方向的组织中,街头诗在动员受众情感方面的作用得到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发挥,通过圈层化的传播方式嵌入根据地群众的日常生活,使其在抗战实践中爆发出巨大的革命热情。
3. 集体协作式的情感传播:从政治动员下沉到文化自觉
街头诗的传播贯穿了晋察冀边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传播历程,这一过程中,工农兵群众具有多重传播身份:既是传播主体,也是传播内容的享有者、传播过程的接受者。 在此,拉斯韦尔所归纳的完整的线性传播过程的起点和归宿达到融合,[26]形成了由知识分子激发、工农兵群众主动传播与自我接收的集体协作式情感传播通路,其情感动员效果呈现出由表及里、自上而下、由政策动员到文化自觉、由知识阶层向工农兵群众传播的过程,情感动员的线索随这一过程逐步深入、扩散。
1939年,以铁流社、战地社等知识分子诗人团体为中心扩展的晋察冀边区街头诗运动初兴时,以政治动员的传播方式为主,政治口号、政策解说与街头诗传播融为一体,在初期街头诗的传播过程中,边区政府、文联对文艺工作的指导为其提供了文艺大众化的明确方向。 随着政治动员的层层深入,街头诗发展在具体的文学传播实践中不断纠偏,逐渐开始从根据地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掘情感动员符号,其情感动员方式也逐步下沉到现实的抗日实践中。
从情感动员的主体来看,街头诗先由知识阶层发起,逐渐带动工农兵群众,从而实现全民情感动员。 田间、柯仲平等街头诗人在《街头诗歌运动宣言》中说:“(街头诗)目的不但在利用诗歌作战斗的武器,同时是要使诗歌走到真正的大众化的道路上去,不但要使有知识的人参加抗战的大众诗歌运动,更要引起大众中的‘无名氏’也多多起来参加这场运动。 ”[27]艾青认为,街头诗“必须成为大众的精神教育工具,成为革命事业里的宣传与鼓动的武器”。 [28]知识阶层作为文学内容生产者与传播者,进行群体内部动员与实现全民情感动员是相辅相成、互为衔接的,前者是促成其传播行为的情感动机,促使知识阶层走出“象牙塔”,走向并动员广泛的工农兵大众,激发其自发、自觉的情感动员。 周进祥回忆孙犁在《晋察冀边区的文艺工作》一文中引用的一首《用黑炭歪歪地涂在破庙墙壁上》的街头诗,将这一情感动员的自觉化、文学传播大众化过程生动地体现出来。
“中国打日本, 月(越)打月(越)有引(瘾), 日本打中国,月(越)打月(越)多梭(哆嗦)。 ”
这首诗虽别字较多,但主题明确、语言朴实、扎根生活,1940年后,街头诗已成为工农兵自发的传播运动。 晋察冀边区工农兵群众多为文盲、半文盲,但已能自发写出具备强烈情感动员偏向且表意连贯的街头诗,进行自觉的情感动员,可见由知识阶层发起的街头诗传播的情感动员已普及深入于工农兵群众中。 在根据地群众创作街头诗热潮中,青少年、儿童也加入了自发创作、传播街头诗的行列,田间提出,街头诗运动所取得的成绩之一便是“一批十几岁的小同志们正由于街头诗运动而走向‘街头诗人’之路”。 [15]朱子奇于1947年发表了他在贾家庄附近村子记录的由工农兵群众自发创作并传播的街头诗,内容多为村里人、村里事。 [29]可见,街头诗通过情感表达进行全民化的复次情感动员,渗透了文化感知,从而形成一种植根于根据地抗战实践、深入根据地群众精神层面的文化自觉,即费孝通所定义的“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与自我创建”。 [30]
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街头诗传播的情感动员效能
媒介的生态隐喻强调媒介环境对人的感知、意识、心理、思维的影响和塑造,[18]媒介对社会的根本影响在于对其意识结构和观念方式的影响。 街头诗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其情感动员效果体现在受众认知、行动层面,亦体现在宏观的社会心态层面。
受众认知与行动层面,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街头诗传播的情感动员塑造了普遍的社会信任,在全民族抗战的目标指引下,转化为政治的共意动员。 布尔迪厄、普南特、福山等社会学家认为,信任本身是一种社会资本,社会信任是其他价值和规范的基础,是社会凝聚力的核心。 [31]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街头诗的媒介形态与传播路径,植根于工农兵群众的日常生活,并依托政府和民间组织进行传播,其接近性、集体性特征使传统社会网络关系中的普遍信任情感被激发,由统一的情感联系凝聚转化为根据地群众社会资本的集合,并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价值规范框架下,实现了以街头诗为中心的公共舆论空间的塑造,使根据地群众广泛、深层地参与到抗战实践中,并自觉将街头诗作为政治表达的传播工具加以运用,从而将社会信任转化为政治的共意动员。
社会心态层面,正如伽达默尔将教化视为一种“极其深刻的精神变革”以及“进行自我回归之路的‘塑形’”,[32]街头诗传播的情感动员对根据地受众的精神教化有着重要作用。 魏巍谈道:“晋察冀,是由一支背着斗笠、穿着草鞋的队伍从日寇手中夺回的土地……我们热爱晋察冀,不仅因为她是抗日的堡垒,而且还因为她是一个崭新的社会,是人民的希望所在。 正是在这里,在硝烟和风沙中孕育着新中国的花朵。 ”[33]正是基于这种积极的社会心态和国民主体性的生发,晋察冀根据地的街头诗虽取材自根据地抗战实践和工农兵生活,却以多样化的传播形态进行大规模、参与式的情感动员,不仅培育了根据地群众作为革命者的理性选择与斗争精神,还培养了其作为民族、国家主体的、具有成长性的国民身份转向与公众趣味。 街头诗的传播最先由知识分子带动,激发根据地群众自我生产、自发传播的文化自觉和情感动员,标志着根据地军民群众在抗战实践中开始自主关注自身命运与国家发展、个体心灵与集体价值间的关系,在高度情感化的理解、传播、参与、共享中推进革命正义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志毓. 情感史视野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研究[J]. 史学月刊,2018(4):14-17.
[2] 白淑英,肖本立.新浪微博中网民的情感动员[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9(5):60-68.
[3] 何道宽. 夙兴集:闻道·播火·摆渡[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205.
[4] 陈晓洁. 从媒介环境学视角对文学传播学研究的思考[J]. 齐鲁学刊,2017(4):157-160.
[5] 杨丽珺. 山西抗日根据地传媒文化特点研究[D]. 山西大学,2007.
[6] 闻一多. 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M]//闻一多. 闻一多全集(三). 上海:开明书店,1948:331.
[7] 赵琴.《新青年》媒介传播的时空偏向研究[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9(3):134-140.
[8] 哈罗德·伊尼斯. 传播的偏向[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26.
[9] 华进,陈伊高. 媒介环境视阈下传播的“媒介偏向论”探析[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21-123,133.
[10] 郭毅. 传媒·仪式·社会:西方学术语境中的媒介事件理论[J]. 新闻界,2018(7):25-32.
[11] 侯耀蓉. 传播学观照下的大众化的街头诗[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1):148-149.
作者:张倩1,庞慧敏2
SCI论文
- 2024-10-23SCI期刊要自己推荐审稿人 推荐谁
- 2023-08-01sci四区发论文最容易吗
- 2023-05-10英文论文的检索号是什么
SSCI论文
- 2023-03-08全球经济趋势分析论文发表ssci期
- 2024-02-02学霸笔记:超级好用的ssci论文发
- 2024-03-22SSCI四区的文学期刊
EI论文
- 2022-08-12发表scopus论文的步骤
- 2022-11-11ei会议论文会拒稿吗
- 2023-05-31纺织类的ei期刊(3-5本)
SCOPUS
- 2023-02-20scopus检索与ei哪个好
- 2023-04-21论文被scopus成功录用需要多长时
- 2023-03-14scopus期刊收研究生论文吗
翻译润色
- 2024-08-17国际中文期刊评职称承认吗
- 2023-05-06基因测序文章怎么翻译润色
- 2022-05-07sci论文润色更容易录用吗
期刊知识
- 2022-03-08火电厂论文外文翻译有什么服务
- 2021-01-16高钾血症论文发表期刊
- 2020-02-07sci期刊发表的论文都可以被web o
发表指导
- 2024-08-17氧菌论文可以投稿的期刊
- 2021-08-07电熔炉相关论文文献看哪些
- 2018-04-04经济学动态发表论文审稿周期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