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当代文学价值观如何构建
时间:2021年03月04日 分类:文学论文 次数:
文学是时代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同时推动着时代价值观念的发展演进。什么是价值观?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价值观是对经济、政治、道德、金钱等所持有的总的看法。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价值观也有所不同。”《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第6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价值观因人而异,处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扩而言之,每个社会都有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反映在文学中,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其特定的价值观。价值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影响文学价值观的因素也是方方面面。在影响中国当代文学价值观的众多因素中,有一个不可忽视,那便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与当代文学相伴生,对当代文学价值观念影响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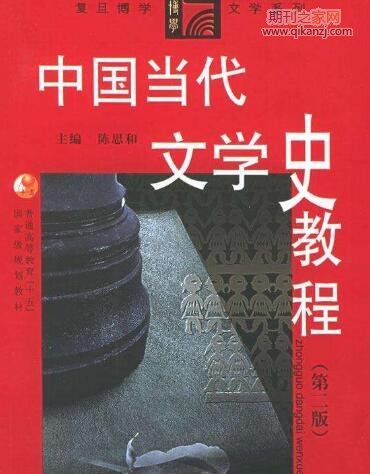
文学方向论文范文: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焦虑困境与出路
这篇世界文学投稿论文发表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焦虑困境与出路,当代文学中存在的焦虑困境和出路是如何产生的呢?这是目前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窘境,论文拟在分析这种焦虑困境如何产生的基础上,指出摆脱困境的出路。
“事实上,虚无主义是一种非常深刻的世界观和学说,其怀疑不仅指向文化、道德、历史、民族等意识形态和现实制度,而且指向宇宙和生命的意义,具有浓郁的形而上色彩。”黄发有:《虚无主义与当代文学》,《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虚无主义既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思潮,又是一种形而下的世俗社会文化思潮。虚无主义对当代文学价值观既有积极的建构作用,但更多的时候,却极具消极性的解构作用。当代文学中,形而上的虚无主义非常匮乏,可谓求之不得;而形而下的虚无主义则比较泛滥,可谓挥之不去。这两种形态的虚无主义都参与到当代文学的价值观念建构,并严重地影响到了当代文学的质量与成就。
因此,对当代文学中的虚无主义思想进行全面梳理和辩证认识,对于我们客观认识当代文学中虚无主义问题的历史由来、存在状况,认识虚无主义对当代文学价值观念的影响,以及如何正确对待虚无主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在当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这种认识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必要性。
一、中国当代文学中虚无主义问题的历史由来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各种虚无主义思潮泛滥,虚无主义作为一个思想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这一方面凸显出虚无主义作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文化思潮,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或困扰日益突出,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学术界对虚无主义的警惕和担忧。
这种关注和讨论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从哲学层面对虚无主义进行理论探讨,指出虚无主义的实质及其发展演变。这种哲学层面的探讨非常多,例如南京大学张凤阳教授的《论虚无主义价值观及其文化效应》,作者认为尼采的“上帝死了”的著名宣言,乃是表明一种重估价值的尝试。由于上帝已死,再无神圣的法庭,“一切皆虚妄”,所以“一切皆有可能”。
这种虚无主义价值观的流行,必然会滋育和助长一种以越界和放纵为特征的行为方式。中国人民大学余虹教授的《虚无主义——我们的深渊与命运?》一文,则系统地指出了虚无主义的几种主要历史形态,并探讨了西方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到列奥·斯特劳斯等人对待虚无主义理论的发展。这样的研究还见于邹诗鹏教授的《现时代虚无主义信仰的基本分析》和吴宁教授的《现代性和虚无主义》等文。另一个是对中国当代社会中弥漫的各种虚无主义思潮的分析批判,这类研究也非常多,主要的如李舫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表征》,作者从社会文化现实出发,概括了当下中国社会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系列文化表征,并对其予以文化批判;杨金华的《当代中国虚无主义思潮的多元透视》则列举了当代中国虚无主义的种种表现,并予以分析批判,等等。众多不同研究的出现,凸显出虚无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的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
在对当代文学中的虚无主义问题展开分析之前,我们仍然有必要来了解一下虚无主义的理论由来。什么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Nihilism)系德文Nihilismus的意译,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Nihil(虚无),意思是“什么都没有”。虚无主义这个词最早出现于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之中,小说的主人公巴扎罗夫“是一个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他认为:“凡是我们认为有用的事情,我们就依据他行动。目前最有用的事就是否认——我们便否认。”〔俄〕屠格涅夫:《父与子》,第228页,丽尼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作为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和否定精神的个体,巴扎罗夫狂热而又片面地追逐西方现代化,否定俄罗斯一切的传统艺术、宗教和伦理道德,因此被人称为“虚无主义者”。
“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在19世纪的俄国和德国非常流行。在19世纪俄国文学中,在普希金、屠格涅夫、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笔下,出现了大量的“多余人”形象,这些人思想空虚、行为乏力、缺乏热情、消极颓废,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和方向,都是一些时代的“虚无主义者”。而把虚无主义这个概念由文学领域引入哲学领域的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F.H.雅各比,他在《给费希特的信》中,首次从哲学角度使用了“虚无主义”这个概念,用以否定超验的理想特征。在西方哲学史上,对虚无主义达到深刻阐述,并把它上升为一种哲学思想理论体系的,是尼采。
尼采关于虚无主义的所有表述,都来源于他的那句惊世骇俗的著名言论:“上帝死了。”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所谓的“上帝乃是表达理念和理想领域的名称”,上帝死了,意味着“一个超感性的、约束性的世界的不在场”,〔德〕海德格尔:《林中路》,第224页,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也即“超感性领域”的死亡。“超感性领域”是对现实所有理性和经验领域的超越,等同于终极价值。既然上帝已死,那么终极价值也就不复存在。
由于失去了终极价值的引领和监督,一切的理想、道德、信仰、价值、理念等都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于是一切皆不可信,一切皆有可能。因此,尼采说:“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没有目的,没有对于目的的回答。”〔德〕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第280页,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既然最高价值已经自行贬黜,那么就有必要重新进行价值定位。于是,尼采就喊出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
继尼采之后,对虚无主义理论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没有认清虚无主义的本质。尼采的虚无主义是对西方自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的否定,但其本身也是这种形而上传统的一部分,他陷入了自我否认的逻辑旋涡,有其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与矛盾。尼采将虚无主义的出路归结为个人的强力意志,而海德格尔则从人的存在来探讨虚无主义本质,为人类的存在寻找依据,为人类寻找精神家园。而对虚无主义做出科学阐释并指明克服途径的是马克思。
马克思从人的解放角度来规避和克服虚无主义,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由人的具体活动构成。“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人类要想实现自我解放,不能寄希望于虚幻的神和上帝,必须依靠自己的主体活动,创造历史,解放自己。马克思的这种唯物论思想,直到今天,对于我们正确对待和克服虚无主义,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虚无主义已经成为我们所处时代的重要文化表征,无法拒绝。西方社会对虚无主义予以深入探讨的哲学家非常多,除上述外,还有福柯、德里达、诺斯、列斐伏尔等,虚无主义俨然成为西方社会的一门显学,如同尼采认为西方社会历史进程本身就是虚无主义的历史进程一样,虚无主义还会伴随着西方社会的历史演进,继续长存并将得到持续关注。
回到中国历史文化语境,虚无主义也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文明进程。中国传统道家哲学中的“无”和佛教文化中的“空”,都指向虚无主义。如老子《道德经》中的“无为而治”思想:“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庄子·逍遥游》中的隐匿遁世思想:“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佛家的色空观念:“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般若波罗蜜心经》),等等。道家和佛家的这种虚无主义思想对中国文化和国民心理影响极深。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金瓶梅》中有着鲜明的“色空”观念,由色入空,由实到虚,一切归结于无;《红楼梦》中则有着浓厚的“虚无”思想,从虚无中来,归于虚无,所谓“好就是了,了就是好”,“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这是虚无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体现。
虚无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广泛存在,表现形式多样。比如鲁迅,虚无主义被视为其思想的根本,是其无穷战斗力量的源泉。与一切旧的恶的力量做斗争,横扫一切,甚至包括灵魂中的旧我,这是鲁迅反抗绝望的虚无战斗精神体现;“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是其孤绝的虚无战斗姿态。鲁迅的散文诗《野草》中弥漫着浓厚的虚无情绪;小说《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等人身上,都有着或鲜明或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五四运动落潮后,整个社会弥漫着浓厚的感伤和虚无情绪,丁玲的《沙菲女士的日记》和庐隐的《海滨故人》对此都有真切的反映,其中的女主人公们纷纷遭受过理想、爱情、事业、婚姻或家庭的挫折,都有着浓厚的虚无主义情绪。
1928年后,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在一些革命作家笔下,虚无主义成为一些革命党人的共同精神气质,如茅盾“《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中系列男女主人公(方罗兰、章秋柳等),都有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迷惘、软弱、动摇的虚无精神特征。而在同时期的巴金笔下,则塑造了大批的无政府主义者形象,如《灭亡》中的杜大心、《死去的太阳》中的王学礼、《电》中的李佩珠等,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其虚无主义精神的特别表现,在其漫长的一生创作中具有某种持续性。20年代作家许地山在其《命命鸟》《缀网劳蛛》等作品中,表达出带有佛家空无和宿命论色彩的虚无思想。早期老舍的创作中,如《赵子曰》《二马》《老张的哲学》等,也表现出世故、油滑和价值相对中立的虚无主义色彩。还有40年代钱钟书的《围城》,借用西方存在主义哲学,表现现代人的尴尬的生存处境——“外面的人想入,里面的人想出”,同样体现出虚无主义的哲理意蕴,等等。总之,虚无主义思想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外来的虚无主义哲学与本土的虚无主义思想相结合,表现形式多样。
1949年后,虚无主义在当代文学中表现为大落和大起。50—70年代,由于与西方世界隔绝,中西文化交流受阻,再加上盲目地破四旧、反传统,不管是来自西方还是本土文化中的虚无主义哲学基本上绝迹。与此同时,对传统历史与文化的漠视却导致世俗虚无主义思潮肆虐横行,极大地伤害了中国文化的元气,出现了后来被阿城和郑义等寻根作家们集体抨击的所谓的“文化断裂带”。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文艺报》1985年7月13日。新时期以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重启,西风再次东渐,当代中国社会各种虚无主义思想重现,并逐步走向泛滥。
一方面,西方各种带有虚无主义倾向的思想学说蜂拥而入,如尼采的唯意志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萨特、卡夫卡和海德格尔等的存在主义哲学等,与历经“文革”后特定的中国社会现实相碰撞,很容易产生共鸣,进而催生出多种形态的虚无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在外来文化的激发下,80年代上半期中国社会出现了“文化热”,本土传统文化得到重新审视,传统道家和佛家文化中的虚无主义思想,部分地得到了重现。而最为重要的是,80年代中国社会思想解放运动不断深入,带来了思想自由和价值的多元化;再加上80年代后期商品经济、消费主义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各种世俗虚无主义思想丛生,逐渐走向泛滥,而那种超越现实时空和欲望狂潮、具有深邃精神指向和终极价值思考的形而上虚无主义,却日渐稀薄了。各种廉价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终于在90年代成为文化界、思想界和学术界不得不严阵以待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和思想问题。
二、中国当代文学中虚无主义的存在形态
近30年来,虚无主义在中国社会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它们解构历史、颠覆崇高、瓦解意义和深度,制造廉价狂欢和喧嚣,误导价值观念,影响极为恶劣。由此,虚无主义被当成一个贬义词,几乎成为众矢之的。实际上,这是不客观的,对虚无主义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在《权力意志》中,尼采将虚无主义区别为两种:积极的虚无主义(PositiveNihilism)和消极的虚无主义(NegativeNihilism),并指出它们不同的表现形态和历史作用。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讲,也存在着两种形态的虚无主义:作为精神哲学的形而上的虚无主义和作为世俗社会文化思潮的形而下的虚无主义。二者形态各异,也有积极和消极之分,需要区别对待。
先看作为精神哲学的形而上的虚无主义。就本质而言,虚无主义是一种哲学意识,是对现实经验的超越、洞彻与指引。哲学与文学密不可分,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都会具有深刻的哲理意识,伟大的小说家往往都是哲学家。总体来讲,形而上虚无主义在当代文学中非常匮乏,可谓求之不得。1949—1976年期间,中西文化交流中断,西方各种虚无主义思想无法继续在中国传播。同时,在唯物主义思想观支配下,各种带有唯心主义倾向的虚无主义思想,包括本土的佛道学说和各种外来虚无思想,都受到否定和批判。这就导致该时期的文学中虚无主义哲理意识非常薄弱,仅在个别作家笔下,偶尔有所流露。例如诗人郭小川,在写于1959年的抒情长诗《望星空》中,表现诗人夜晚在长安街头仰望星空,通过个人、生命与宇宙的对比交流,感受到个人力量有限而宇宙浩瀚无限、个人生命短暂而宇宙生命永恒,从而生出惆怅之感:“在伟大的宇宙的空间/人生不过是流星般的闪光。
在无限的时间的河流里,/人生仅仅是微小又微小的波浪。/呵,星空,我不免感到惆怅,/于是我带着惆怅的心情,/走向北京的心脏……”联系1958年“大跃进”的历史背景,这样的思考无疑是对当时不断膨胀的历史主体盲目自信的一种纠偏,同时这种具体与抽象、个体与整体、有限与无限、短暂与永恒的对比,也使诗歌呈现出一种形而上哲理思考,从而获得了超越性的艺术价值。但这首诗歌在当时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原因就是认为其中“宣扬了神秘主义、虚无主义”,认为作者表达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幻灭感。华夫:《评郭小川的〈望星空〉》,转引自张恩和:《郭小川评传》,第11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而在今天看来,这种“神秘主义、虚无主义”的思考表达,恰恰正是这首诗歌的艺术生命力和价值所在。70年代的地下诗歌中,像北岛的《回答》和顾城的《一代人》等,充满了怀疑和否定精神,也体现出某种虚无主义哲理意蕴。只不过,在50—70年代文学中,这样的虚无主义表达非常有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重启,思想解放不断深入,文化思想日渐多元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虚无主义有所复归。对一些作家来讲,虚无主义成为其规避主流话语束缚、拉开文学与现实距离、反顾自身乃至思索人类和宇宙存在问题的思想武器。对此最早进行思考的是王蒙。“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由于自身特定的历史遭遇,王蒙对革命、理想、信仰和个体命运之间的关系反复咀嚼,从中提炼出某种虚无主义哲理意蕴。《蝴蝶》中,主人公张思远在不同人生阶段,经历了从小石头、张指导员、张书记、老张头和张副部长等的身份变迁,以致自我迷失。
作者借用“庄周梦蝶”典故,表现了在历史变动过程中主人公的自我困惑——究竟“我是谁”?这是一种存在主义的哲理困惑,正是同时期宗璞小说《我是谁?》所要探究的问题。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则通过主人公倪吾诚荒诞而又悲剧的人生遭遇,表现了其肉体和精神的分裂。这是又一个“方鸿渐”式的知识分子,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位置和价值,作者对其给予了存在主义的哲理审视。而在海德格尔和萨特等存在主义大师看来,存在主义在本质上是对人的存在的虚无,是虚无主义的一种。海德格尔从客观角度,而萨特则从主观角度,确认了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在本质上都是虚无的。
除王蒙外,80年代以来,能够从形而上层面进行虚无主义哲理思考的作家并不多,主要还有残雪、张承志、史铁生、北村和格非等人。残雪的小说深受卡夫卡影响,以现代派艺术表现手法,表现人的恶劣生存境遇和孤独本质,格调阴冷,传达出一种透骨般的虚无主义气息。荷尔德林说,“人,在大地上诗意栖居”,而残雪则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存在。在《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公牛》《黄泥街》等作品中,残雪一方面表现了人的生存环境的肮脏可怖,其中充满了蛇、苍蝇、老鼠、蜈蚣、蛆、蝙蝠、蜘蛛等肮脏恶心动物,而且天空老是下着墨色的雨,阴暗潮湿发霉。
这样肮脏恶劣的环境,从客观上否定了人的诗意存在。另一方面,残雪还否定了人的社会存在,形象地诠释了“他人即地狱”这一存在主义哲学理念。她笔下的人物,一个个如同神经质,相互嫉妒、猜疑、窥视、提防,充满敌意,互相折磨乃至互相伤害,哪怕夫妻、母女和父女之间也是如此。残雪无情地撕破了现代人的人性面具,展示了人性的丑陋和扭曲。不仅如此,残雪的小说还拒绝人性救赎,不给人物以任何自我拯救的可能。她笔下的人物不管如何努力,如何挣扎,都无法自我改变,找不到出路,更看不到希望。这种虚无主义的书写,使残雪的小说直逼人的存在本质,引人思考。
残雪的虚无主义给人感觉阴冷,而张承志的虚无主义则让人感觉炽热。张承志的虚无主义源自于他的理想主义和宗教情怀,表现为以理想取代现实、以精神(信仰)代替物质,表现出对人的现世存在的漠视和对人的精神世界(宗教信仰)的迷狂。张承志早期的充满了理想主义气息,在《绿夜》《黑骏马》《北方的河》等作品中,其圣洁的理想与污浊的现实之间严重对立。理想很浪漫,现实很骨感:“生活露出了平凡单调的骨架,草原褪尽了如梦的轻纱。”(《绿夜》)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张承志采取的策略是“抓住生活中的那瞬间的美”(《绿夜》),用瞬间的美感体验来超越或遮蔽对芜杂现实的痛感体验。
这就是张承志所一再倾心的美学——“美丽瞬间”。樊星:《在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这其实是一种形而上的虚无主义体验,是在瞬间的自我陶醉中实现对现实的超越。从根本上讲,“美丽瞬间”追求的是一种唯美主义审美体验,而唯美主义本质上是颓废的、病态的,是虚无主义的特定表现。张承志的另一部分,如《黄泥小屋》《残月》《九座宫殿》《心灵史》等,则表现出强烈的宗教色彩,以虚幻的精神(信仰)追求碾压或取代人的物质存在,其虚无姿态已经逐渐走向极致。
史铁生的虚无主义则充满智慧和神性,是勘破命运后的大彻大悟。由于年轻时双腿突然瘫痪,史铁生几乎一辈子都在思考命运问题,愤懑感慨:“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我与地坛》)这是其宿命论认识由来。宿命论是一种消极的唯心主义认识观,是对现实多样性和或然性的否定,在本质上是虚无的。史铁生认为:“人的苦难,很多或者根本,是与生俱来的……这正是上帝的启示:无缘无故的受苦,才是人的根本处境。……正如存在主义所说:人是被抛到世界上来的。人的由来,注定了人生是一场‘赎罪游戏’。”所以,“我越来越相信,人生是苦海,是惩罚,是原罪。”史铁生:《宿命的——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书面讲稿》,《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1期。
这种认识正是克尔凯戈尔的悲观主义哲学观点,而悲观主义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一种,是对现实人生的怀疑与否定。同时,史铁生还对人的生与死、有限与无限、惩罚与救赎等问题反复思辨,体现出浓厚的存在主义色彩。例如,《我与地坛》对生与死的探讨就受到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生死观的影响,作者认为“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而海德格尔则认为“死在生存论上等于说:向死生存或向死存在”。〔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65页,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正是因为死的存在,才凸显出生的意义。《命若琴弦》深受加缪西西弗斯神话的影响,并从中提炼出一种过程论的生存哲学。这种思考,使史铁生的超越了个人的苦难现实,具有普泛的形而上哲理深度。在长期的精神冶炼中,史铁生创立了一种个人宗教——一种介于基督教和佛教之间的宗教,史铁生(遗作):《昼信基督夜信佛》,《收获》2012年第2期。试图用宗教理念来对抗虚无,给人提供出路。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中,他就试图运用基督教的忏悔与佛教的悲悯来对人的灵魂进行救赎,为充满原罪感的当代人寻找精神出路。在当代作家中,能够从宗教或神的高度对人的彼岸世界进行关怀的作家很少,史铁生算是难得的一位。
另一位具有宗教情怀的作家是北村。北村的属于典型的基督教,是对基督教义的演绎,这在他的代表作《施洗的河》中表现得很明显。格非的则充满宿命论色彩,如《迷舟》《敌人》《人面桃花》等,人物的命运似乎冥冥之中早已注定,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结局都是走向失败或虚无。这体现了格非的世界观,也让他的作品获得了一种形而上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品格。
总体来讲,当代文学中形而上虚无主义非常匮乏。与之相比,形而下的世俗虚无主义思潮却很多。
SCI论文
- 2024-06-19COMPUTER GRAPHICS FORUM期刊简
- 2024-07-11sci论文接收后多久下doi号
- 2024-01-03今日话题:sci审稿状态“reject
SSCI论文
- 2024-01-11发表ssci论文可以破格晋升吗
- 2023-03-06新闻与传播学SSCI期刊
- 2024-10-12ssci论文申请撤稿什么时候能转投
EI论文
- 2023-02-07ei会议提前多久开始征文
- 2023-02-01国际性ei会议都是英文吗?
- 2024-02-21计算机视觉方向论文怎么发EI快
SCOPUS
- 2023-03-24scopus收录论文速度怎么样
- 2023-04-12scopus数据库收录哪些门类的文献
- 2023-09-12如何发表Scopus论文技巧分享
翻译润色
- 2023-05-09锻造相关中文文章怎么翻译为英文
- 2022-03-31英文期刊编辑回复论文表达不行怎
- 2024-08-16国际中文期刊发表论文应该用什么
期刊知识
- 2018-03-15学报上发表论文最早多久见刊
- 2017-05-11机械工程方面论文要加急发表去哪
- 2024-09-29中文核心期刊投稿要推荐审稿人吗
发表指导
- 2018-09-29不锈钢热处理论文适合投的期刊
- 2024-08-16工程监理人员怎么选刊并投稿
- 2015-07-10如何向核心期刊投